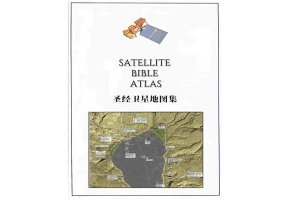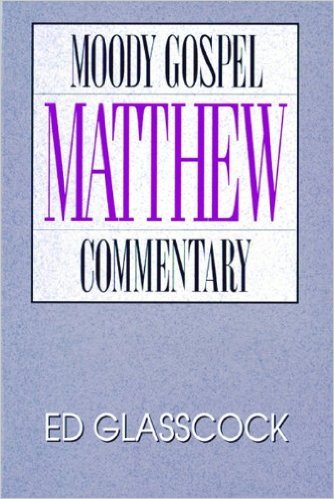第四章:自然界是圣经的第67卷书吗?
理查德·梅休(Richard Mayhue)
我第一次见到魏德孔博士是在1971年1月。当时我刚刚信主,还是一名现役海军军官,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斯科特纪念浸信会教堂参加了他与亨利·莫里斯博士共同举办的创造论讲座。1971年8月,我辞去美国海军军官的职务,去印第安纳州威诺纳湖市就读于恩典神学院,坐进魏德孔博士的课堂里学习《约伯记》。随后,他成了我在恩典神学院的神学硕士(Th. M.)和博士(Th. D.)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他坚定的信仰不仅成为我在学生时期的榜样,而且当我初出茅庐在恩典神学院执教(希腊语和新约)的早期,他作为高年资同事,也一直极力鼓励着我个人的成长。我最珍贵的回忆中有一些是来自他担任我的教工祷告伙伴的时候。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因为认识了“杰克”·魏德孔这位良师益友,得着了极为丰盛的生命。
在魏德孔博士一生的的教学和写作事工中,他都将提摩太前书4章7-8节和犹大书3章的教导看得十分重要。当他不知疲倦地为一次性交付圣徒的信仰而奋战,全心全意地打那美好的仗,并持续不懈地高举圣经时,他已经作为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一位杰出而清晰的代言人奔跑在那不停息的赛场,尤其是在创造[1]、创世记大洪水[2]和旧约的历史性方面。[3]
魏德孔博士在过去四十年里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出于对这位特别之人的崇敬,我欣然命笔,在一个他曾为之殚精竭虑的主题上继续建造,就是确认和捍卫年轻地球论。魏德孔博士,我向你献上本章略表敬意,因为你曾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无私地投身事奉,效忠于上帝在他绝对无误且全备的话语——《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徒20:27)。
问题
自然界是圣经的第67卷书吗?要回答这个挑衅性的问题乍听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上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它涉及到:(1)圣典的构成;(2)对诗篇19篇、使徒行传14章、使徒行传17章、罗马书1章和罗马书10章的正确解释;(3)《圣经》的独特权威;(4)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在性质上的异同之处;(5)人类堕落的思维和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6)恰当的释经学原则;以及(7)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对这一重要问题不应掉以轻心,也不应草率回答。然而,休·罗斯博士[4](Dr. Hugh Ross)似乎正是轻心地、草率地处理这件事的。在一篇篇幅不足三页的讨论中,这位人气颇高的作者毫无批判地、毫无保留地写下了一个看似不证自明的公理,“自然界的事实可以比作《圣经》的第六十七卷书。” [5] 读者当如何理解休·罗斯的断言?他说得对吗?或者,他错了吗?
休·罗斯的断言——可靠还是可疑?
休·罗斯用了六个简短的段落和一张小表格,[6] 对这个深刻的问题轻描淡写,然后就给出 “绝对如此!”的回答,毫无保留,毫无迟疑。除了他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引用任何权威来支持他那相当武断的回答。表面上看,他的断言似乎足以证明他的答案,然而对一个较熟悉《圣经》的人和/或一个受过批判神学思想训练的人来说,休·罗斯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五个:
首先,休·罗斯的表格[7]包括23处经文,据说这些经文证实了他的答案,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结果却令人失望,这些只是对圣经文本的断章取义(即引用圣经文本来支持自己的结论,但通过更为细致的检查后发现,文本或与所提出的观点并不直接相关,或实际上是矛盾的)。以下观察指向这一结论。
1. 传道书3:11和罗马书2:14-15所论述的是在人良心中的普遍启示,而不是如休·罗斯断言在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
2. 罗马书10:16-17和歌罗西书1:23提到的是人类传扬福音的活动,而不是像休·罗斯所说自然界的一般启示。
3. 诗篇50:6(天堂是指天使)、85:11(耶稣王的属性)、97:6(天堂是指天使)、98:2-3(上帝与以色列的交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正确的可能性比起休·罗斯所暗示的自然中的普遍启示的可能性来说差不多,或者更大。
4. 箴言8:22-31是一篇拟人化的“智慧女士”的演讲,而不是像休·罗斯所说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
5. 约伯记10:8-14、12:7、34:14-15、35:10-12、37:5-7、38-41、诗篇8、104、139和哈巴谷书3:3所论述的是一个人能从圣经的特殊启示中学到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而不是像休·罗斯所教导的那样,是一个人能从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中学到的知识。
6. 只有诗篇19:1-6、使徒行传14:17、17:23-31和罗马书1:18-25、10:18确实提到了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只有这些是与休·罗斯的话题相关的经文。
所以,休·罗斯在“自然界是圣经的第67卷书吗?”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在他引用的23处经文中,只有5处(22%)似乎支持了他的基本观点,然而也并没有达到休·罗斯所暗示的深度或广度。其他78%的经文被他误解误用。这一连串的错误洪流,迅速冲蚀了人们对休·罗斯客观而熟练地解读《圣经》的能力。
其次,休·罗斯声称在罗马书10:16-17[8]和歌罗西书1:23[9]中提到通过自然界的一般启示向全世界传扬福音。然而,即使粗略地阅读罗马书10:16-17的经文也能得知保罗显然是在谈论圣经中的福音(即“基督的道”,是由人类的传教士传扬的)。虽然《歌罗西书》1:23的解释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保守的福音派解经家的共识是,保罗指的是人类传扬的福音,要么是用夸张的手法指代当时已知的世界,要么是预感福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10]
第三,休·罗斯对于普遍启示的理解和应用是错误的。正如上面第一点和第二点所指明的,休·罗斯本是学天文的,通过对经文的错误解释,提出了对普遍启示的宽泛的哲学处理方式。他甚至暗示,在“科学”领域所发现的一切都是普遍启示,因此,在价值和质量上与圣经的特殊启示是相等的。休·罗斯在没有任何理性推导或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圣经教导的是一个双重的、可靠一致的启示。”[11] 他要借此暗示普遍启示不仅在其启示的质量上与特殊启示是平等的,而且在其权威上也是平等的。因此,他认为普遍启示,即任何可发现的科学事实,实际上有解释圣经的权威,而不是相反(根据圣经去解释科学发现)。
关于普遍启示的主题将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详细地讨论。然而,一些初步的观察足以证明休·罗斯的观点有缺陷。
1. 《诗篇》19篇确实比较了普遍启示(19:1-6)和圣经的启示(19:7-11)。但事实上,这样的比较突显了其中的不同,而不是像休·罗斯所教导的那样被看作两个绝对平等的事物。《诗篇》19篇反而将《圣经》尊为上帝的启示中更伟大和最有价值的。
2. 休·罗斯把科学和《圣经》放在同一个层次上。科学是靠人解释的关于自然界的不确切的事实,而《圣经》是由上帝赐予和解释的关于上帝的确切事实,休·罗斯没能将二者区分开来。由于科学并不具有像《圣经》那样准确无误的性质,不难看出休·罗斯大大高估了自然和科学,而严重低估了《圣经》的价值。
3. 他扩展了普遍启示的概念,使之包括了圣经以外所有可发现/可知道的信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圣经中提及这个主题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段落(如诗19:1-6、徒14:17、17:23-31、罗1:18-25和10:18),便看出普遍启示作为上帝启示的合法来源,其范围和目的是有严格限制的。
让笔者简单地就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提两个问题,以证明上帝的意图是使其服务于更狭窄的目的,与《圣经》在信息量和权威上的广阔范畴截然不同。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有普遍启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和一个读《圣经》的人认识的上帝一样吗?[12] 第二个问题,一个人能否仅凭普遍启示就被救赎?[13]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响亮的“不!”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将小者提升为与实际上的大者相同的,甚至更高的地位?
莫里斯和魏德孔早在三十年前就预见到了休·罗斯的主张,[14] 当时他们观察到:
“人们常常以为,上帝给了我们两个启示,一个是自然启示,一个是圣经启示,并且它们不能互相矛盾。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当一个人潜意识中把自己对自然界的解释等同于自然启示,然后谴责那些不愿意把圣经启示塑造成符合他对自然界的解释的神学家时,他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毕竟,特殊启示超越了自然的启示,因为只有通过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正确地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15]
第四,休·罗斯断言,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具有《圣经》一样的“默示”性,[16] 他将提摩太后书3:16应用于此。虽然因为源头是上帝自己,他的所有启示都是真实的、不可辩驳的,[17] 但是只有《圣经》在圣经意义上是“默示”的,即圣灵引导人们以书面形式准确无误地记录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彼后1:21)。此外,《圣经》仅就其自身断言,因为它是“默示”的,所以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第17节继续作为第16节的“目的”解释。当然,甚至连休·罗斯都不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启示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7)。
第五,在《圣经》之上添加任何额外的启示,都使所谓的“自然事实”成了正典。[18] 因此,当休·罗斯认为自然界是圣经的第67卷时,他实际上是在称圣经是不完整的,并因此重新开放正典以添加额外的启示。
我们确定上帝是否会用第67卷书来扩充我们现在的《圣经》吗?或者换句话说,“正典是永远关闭了吗?”几个世纪以来,几项重要的观察使教会相信,《圣经》的正典其实已经关闭,永远不会重新开放。
1. 启示录是《圣经》所独有的,它以无与伦比的细节描述了在永恒之前的末期事件。正如《创世记》作为《圣经》的开篇,用其特有的、详尽的创造记述,将永恒的过去弥合到时间/空间的存在中(创1-2)一样,启示录也从时间/空间转换回永恒的未来(启20-22)。《创世记》和《启示录》因其内容而成为《圣经》完美匹配的头尾(即正典的“阿拉法和俄梅戛”,开始和结束)。
2. 正如在《玛拉基书》完成《旧约》正典后上帝的预言走向沉默一样,在约翰完成《启示录》后,也出现了对应的沉默(甚至直到今天)。由此得出结论,《新约》正典也随之关闭。
3. 因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出现过旧约或新约的意义上的经上帝授权的先知或使徒,所以就没有了之后默示的正典性启示的潜在作者。
4. 在四条禁止篡改《圣经》的诫命中(申4:2、12:32、箴30:6),只有《启示录》第22章18-19节中警告说,上帝会严厉地审判违命者。此外,《启示录》是《新约》中唯一以这样的告诫结尾的书卷。因此,这些事实强烈表明《启示录》是《圣经》正典的最后一卷书,而现在这卷书已经完成,任何的增加或删减都带来上帝极大的不悦。
5. 最后,早期教会(即在时间上最接近使徒的教会)认为《启示录》是对上帝默示的著作——《圣经》的总结。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也应该相信正典已经关闭并且将一直保持关闭,因为根据《圣经》,未来将不再有第六十七卷书,自然界本身也不行。
在总结本节时,读者应该考虑到,如果休·罗斯对科学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一样不精确,那么他的科学也应受到高度怀疑。例如,他写道:“有些读者可能会担心我是在暗示,上帝通过自然界的启示与他通过《圣经》的启示处于同等地位。”[19] 有些人可能会在这点上为他辩护,他们回答说,我们无需为此担心,因为休·罗斯并没有将二者等同,他被误解了。但是,在随后的下文中,这位科学家实际上是在说:“不要担心我将两者放在相同的地位,人类的推理会引导人们勇敢地这样做。” 他实际上是在努力安抚那些他试图劝服的人,将自然界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等同起来是完全合法且无害的,甚至是正确的做法。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有缺陷的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没有得到神圣启示适当的帮助和权威的引导,因此是错误的,并且与《圣经》的实际教导背道而驰,这将在下面的讨论中得到阐明。
探索
阐明了休·罗斯关于自然界是圣经的第67卷书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不等于证明了自然界就不是圣经的第67卷书。我们还必须就至少六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严谨的考查,从而证明这种否定的答案符合事实、公正且合乎逻辑。只有在认真地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才能构建并陈述一个有把握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将依次讨论这六个方面:1)经文; 2)《圣经》的权威; 3)启示的性质; 4)人类堕落的思想和经验主义;5)恰当的释经学以及 6)符合圣经的世界观。
经文
只有七处明确的经文触及普遍启示这个问题(诗19:1-6、传3:11、徒14:17、17:23-31、罗1:18-25、 2:14-15、10:18),[20] 这是许多神学家的共识。这些经文都没有被激烈争议的文本变体,也没有真正有吸引力的不同解释,鲜少例外。因此,这些经节为发展一个释经学基础、并在此之上建立关于普遍启示的神学,提供了理想的无可非议的证据。
这几段经文包含了圣经的特殊启示中关于普遍启示的全部教导。[21] 因此,关于圣经所教导的普遍启示的神学都必须源于这些经文。这就要求我们只能用上帝的特殊启示来定义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启示,而不是让人类的哲学推理污染了这个课题。接下来是对每处圣经经文的简短讨论。
诗篇19:1-6[22]
这篇伟大的诗篇为普遍启示提供了六大见解。首先,就普遍启示的来源而言“诸天”组成部分(19:1)。其次,就普遍启示的内容而言,把创造诸天的荣耀归于上帝是毋庸置疑的(19:1)。第三,只要受造界尚且存在,白天和黑夜的循环就会永不止息,这说明了普遍启示的永恒性(19:2)。第四,就普遍启示的特征而言,它是一个由现象学证据构成的无声见证(19:3)。第五,普遍启示的“量带”不受地理限制,因为证据无处不在(19:4a,b)。第六,关于普遍启示的秩序或规律,日出和日落的可预见性指向受造界的精确次序,从而也说明造物主的有序性(19:4c-6)。
然后在第7-11节中,《圣经》中特殊启示的广阔性与“诸天”中普遍启示严重的局限性(信息的范围和意图)形成了对比。首先,特殊启示的来源是上帝的话语(19:7-8)。第二,特殊启示的信息是救赎(19:9-14)。第三,在永久性方面,特殊启示将比受造界更持久(赛40:8、太24:35、可13:31)。第四,《圣经》的本质是命题性的(即词、句、段等)(诗19:7-8、提后3:16)。第五,特殊启示的范围上达天、下至地(诗19:7-8、119:89)。第六,关于《圣经》的掌控,它是由神的灵完美地引导的(诗19:7-14、提后3:16-17、彼后1:20-2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篇》19篇是经典之作,它明确教导《圣经》的特殊启示优于自然界的普遍启示。因此,在上帝使用《圣经》的特殊启示解释普遍启示的过程中,这段经文首先出现并不奇怪。《诗篇》19篇的结论是,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文化中,普遍启示的信息都是以非言语方式传递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权能和秩序的上帝的存在,因此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他。
传道书3:11
所罗门写下了一个简短而深邃的真理:永恒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创1:27),后来在堕落中被严重扭曲(创3:1-21),因此人需要通过上帝仁慈的拯救来恢复(罗3:21-26)。这暗示了保罗后来更清楚地揭示的真理,即普遍启示“原显明在人心里”(参考罗2:14-15)。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对上帝存在的有限的直观意识,这表明人是不朽的,而不是暂时的。必须进一步指出,这一处经文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讨论的问题,因为它不涉及自然界,而是涉及人的良心。
使徒行传14:17[23]
在这里,保罗拒绝了人们对自己的崇拜,人只能单单敬拜上帝,因为他创造天地(14:15)。他接着就陈述上帝的普遍启示,提到 “从天降雨”的(参看伯5:10、太5:45)和“赏赐丰年”(参看创1:14,29)。这两个现象作为一个持续的明证,借着食物和欢乐满足人类的心(徒14:17),上帝不断地向人类启示自己良善的本性(尽管人类邪恶)。
透过这节经文可以发现普遍启示的几个特点。首先,它贯穿历史,从开始到结束。其次,它是提供给全人类的。第三,它可以被毫无科学素养之人观察到。第四,它揭示了上帝的本性。
使徒行传17:23–31[24]
保罗在雅典——那时最大的知识分子聚集中心之一。尽管雅典人学识渊博,使徒保罗还是指责他们是精神上的无知者(17:23,30)。然后,他向他们挑明上帝作为造物主(17:24)、维持者(17:2 5)、君王(17:26)、救主(17:27)和生命源泉(17:28-29)的真理。
这段经文的主要和明确的重点是神通过保罗的讲道(参见17:23,“我现在告诉你们”和17:30,上帝现在“吩咐各处的人”)和基督复活(17:31)所给人的特殊启示。次要的和含蓄的重点是针对最普遍的启示,就是保罗在讲道中所提到的,上帝是人类的源头。在关于普遍启示的七处标志性经文中,这段经文的贡献最小,因为它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特殊启示,也就是基督的奇迹性复活和圣经中使徒保罗的见证,让我们可以了解普遍启示。
罗马书1:18-25
保罗在这里比较了两重启示(apokaluptō),一重是关于上帝的公义的启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1:15-17);另一重是关于“上帝的忿怒”(1:18-3:20)的启示,上帝的愤怒临到了人的身上,因为人们拒绝了看得见的东西(即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罗1:18-3:20)。他们所能了解(gnōstos)的关于上帝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上帝自己是他们认知的源头(1:19),这些认知是从观察上帝的创造(1:20)而来的。造物主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看得见的所造之物便可以明白无误地彰显出来,叫所有的人无可推诿(1:20),就是那些不荣耀上帝(1:21),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1:25),敬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1:23,25)的人。因为这种拒绝和悖逆,上帝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使徒行传14:17中所得出的三个结论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从创世到现在,上帝已经在受造界中显明了他自己。这种启示对全人类都是触手可及的。要理解上帝关于自己的信息,并不需要专业的科学知识或仪器。
罗马书2:14-15
在这里保罗似乎以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暗指一种内在的感觉(参见2:15中的“是非之心”),这与外在的受造界的普遍启示形成对比。他认为,即使不信的外邦人没有律法(即旧约律法),他们仍然有某种道德标准指导他们的生活。这似乎与传道书3:11中的思想类似:亚当堕落后,人所具有的上帝之形象严重受损,但没有被消灭。上帝在所有人当中仍然有一个内在的见证,这种见证通常指向公义的上帝。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处经文并没有涉及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而是论及人类良知中的普遍启示——即人类灵魂中关于上帝及其道德标准的启示。
罗马书10:18
保罗引用诗篇19:4,强调即使没有传道者,人类也不会不认识上帝。他们会通过普遍启示认识上帝(参见诗19:1-6)。罗马书10:18提到的普遍启示与10:14-17中教导的特殊启示(布道)形成对比。
这最后一处关于普遍启示的经文又回到了诗篇19篇开篇的经文,上下文的顺序有所颠倒(关于普遍启示的诗19:1-6和关于特殊启示的19:7-11;关于特殊启示的罗10:14-17和关于普遍启示的10:18)。
小结
从《圣经》中可以得出以下关于普遍启示的理解:
1. 内容仅限于有关上帝的知识,而不是所有的知识。
2. 时间跨度是整个时间长河,而不仅仅是最近的一段时间。
3. 见证是给所有人的,而不仅仅是一些受过科学训练的人。
4. 获得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的视觉和感觉,而不是用科学的仪器或技术。
5. 全部的普遍启示在创世后立即可以得到。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发展而累积。
因此,关于《圣经》所定义的自然界普遍启示的概念不应该被拓展到这五处特殊启示的经文(诗19:1-6、徒14:17、17:23-31、1:18-25、10:18)所允许的范围以外。扩大普遍启示的概念,就等于在没有上帝的授权的情况下扩充圣经——这是不可思议的。[25] 因此,《圣经》本身拒绝自然界是圣经第67卷书的观点,休·罗斯的断言是错误的。[26]
圣经的权威[27]
权威的概念被透彻地编织在了《圣经》的文字中。这一点从创世记1章1节中(“起初上帝创造……”)到启示录22:20(“是了,我必快来”)之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显明无误地看出。这种“终极权力”的观念与上帝的主权密不可分(罗11:36)。
对于权威的真正了解不是来自《圣经》之外,而是源于《圣经》内部。因此,它不是一个被宗教借用的世俗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关于上帝真正身份的神圣要素。《圣经》关于权威的正确教导,实际上被这个世界的制度丑陋地扭曲了,被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错误地利用了。
到了21世纪初,正确的权威概念举步维艰。从政治极权主义的非法滥用到由后现代自私心态滋生的个人权威,到处都是不正当行使的不正当形式的权威。
讨论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是首先对权威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特别是正当行使的合法权威。一部有代表性的字典将权威定义为“强制服从的权力或权利;道德或法律上的优势;发出命令或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利。”[28]
伯纳德·拉姆(Bernard Ramm)提议:
“权威本身是一种权利或权力,或者发出指令让人执行或服从,或者确定信仰或习俗,期望权威之下者顺服;权威要对权利或权力的主张负责任。”[29]
新约里被译成“权威”的名词最常见(出现102次)的是ἐξουσία(exousia)。一部有代表性的词典将之定义为“统治者或其他居高位者行使职能的权力。”[30]
然而,从圣经的世界观来看,最初和最终的权威属于且仅属于上帝。上帝的权威不是继承来的——没有人可以传给他。上帝的权威不是领受得来的——没有谁可以授予他。上帝的权威不是选举而来的——当时还没有人投票给他。上帝的权威不是攫取的——也没有偷窃的对象。上帝的权威不是赢来的——权威已经属于他。权威是上帝的固有属性,因为他是那伟大的“我是”(出3:14、约8:58)。
考虑到以下三个事实,上帝的权威是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首先,上帝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创1-2)。其次,上帝拥有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诗24:1)。第三,上帝在他所说的“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中,最终要把这一切都消灭了。(启21:5)。
理解和接受上帝权威的事实,就像接受上帝存在的事实一样简单。罗马书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罗13:1)。这节经文清楚地解释了所有权威的来源,并阐明了“神赐权柄”的原则(参见伯34:13;约19:11)。
旧约中有许多明确证实上帝权威的陈述。例如,“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诗62:11)和“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代下20:6)。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犹大写道:“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25)。
这一真理以三段论的方式展开如下:
1.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2. 上帝的话具有权威性。
结论:《圣经》具有权威性。
本体论基础(上帝存在)和认识论基础(上帝只说真理)都是在《圣经》中确立的(创1:1、诗119:142,151,160)。约翰·弗拉姆(John Frame)简洁地断言:“没有更高的权威,没有更确然之根本……《圣经》的真理性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第一前提。”[31] 因此,上帝和上帝话语的本质不是用人类的理性归纳出来的,而是从《圣经》的证言中演绎出来的(参见诗119:89;赛40:8)。
上帝在圣经里展现的权威可以归纳为一系列否定(它不是什么)和肯定(它是什么)的陈述。
1. 圣经的权威不是人赋予的次生权威,而是上帝的原本权威。
2. 它不随时代、文化、国家、民族背景而变化,而是上帝不变的权威。
3. 它不是许多可能的属灵权柄中的一个,而是上帝独一的属灵权威。
4. 它不可以被成功地挑战,也不能被合法地推翻,是上帝的永远的权威。
5. 它不是相对性的或从属性的权威,而是上帝的终极权威。
6. 它不仅是一种提示性的权威,更是上帝的强制性权威。
7. 忤逆上帝的权威不是无所谓的,而是后果严重的。
虽然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和《圣经》一样具有权威性,因为两者来自同一个权威(即上帝)。但是普遍启示不能自证,因此其权威性只能在特殊启示为之确认的范围之内被接受。人对自然界中普遍启示的权威性的理解,不应该超过《圣经》所明确的范围。
休·罗斯如果认可这一圣经真理,他将不得不撤回他断言的,“自然界……与上帝通过《圣经》话语的启示地位相同。”[32] 他也必须承认他的论点,“圣经教导的是一个双重的、可靠一致的启示”,是错误的。[33]
启示的特点
要充分地把握普遍启示[34]与特殊启示在性质与功能上的差异,只需考虑两者之间的三个对比。首先,自然界中普遍启示的世界将会灭亡(赛40:8、太24:35、可13:31、路21:33、彼前1:24、彼后3:10),但特殊启示的话语不会废去,因为它是永恒的(诗119:89、赛40:8、太24:35、可13:31、路21:33、彼前1:25)。第二,自然界中普遍启示的世界是被诅咒的,被堕落所捆锁(创3:1-24、罗8:19-23),因此不是上帝最初创造的完美世界(创1:31),而特殊启示的话语是上帝默示的,因此总是完美和神圣的(诗19:7-9、119:140、提后3:16、罗7:12)。第三,与《圣经》中多维的特殊启示相比,自然界中普遍启示的范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请再考虑更多的差异。
|
|
圣经中的普遍启示 |
圣经中的特殊启示 |
|
11. |
只定罪。 |
定罪且救赎。 |
|
22. |
与特殊启示相一致,但不提供新的信息。 |
强化并详细解释普遍启示的内容,但远远超出普遍启示的范围。 |
|
3. |
它所蕴含的信息需要《圣经》来证实。 |
《圣经》宣告自己是上帝的话语,是自我印证和自我确认的。 |
|
4. |
需要根据特殊启示来解释。 |
不需要其他启示来解释——它自我解释。 |
|
5. |
根据《圣经》的教导,它与《圣经》的地位绝对不相等。 |
无可比拟。 |
有鉴于此,请考虑休·罗斯将自然界视为“他在天上地上所写的话”的要求。[35] 首先,世界的自然启示并不是像《圣经》那样用“话语”来揭示的。其次,在《圣经》中,自然界的普遍启示从来没有被称为上帝的话语,但《圣经》经常被称为上帝的话语(徒7:38;来4:12;彼前1:23)。
休·罗斯认为,自然界和《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在所有方面都平等。这种逻辑就好比说在物质世界里,婴儿和21岁的运动员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因此都完全有能力参加奥运会。这显然是荒谬的,虽然两者都是人类,但它们拥有的体能截然不同。
人类堕落的心智与经验主义
启示不包括人自己发现的东西(即知识),而只包括神所揭示的人自己找不到的东西。在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如特殊启示所限定的,揭示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力量和智慧、上帝的仁慈和人性的堕落(邪恶)。
创世记3章中记载,人类堕落时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后果是灵性的衰退。《新约》用了12个不同的负面希腊文词语来形容人类智能的毁坏。
|
1. 邪僻——罗马书1:28 |
7. 迷惑——歌罗西书2:4 |
|
2. 刚硬——哥林多后书3:14 |
8. 妄——歌罗西书2:8 |
|
3. 瞎——哥林多后书4:4 |
9. 欲心——歌罗西书2:18 |
|
4. 虚妄——以弗所书4:17 |
10. 坏了(心术)——提摩太前书6:5 |
|
5. 昏昧——以弗所书4:18 |
11. (心地)坏了——提摩太后书3:8 |
|
6. 敌对——歌罗西书1:21 |
12. 污秽——提多书1:15 |
由于心智的严重伤残,人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后3:7)。有人甚至“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10:2)。造成这种整体性心智创伤的原因是夏娃质疑和篡改上帝在创世记2:17中的特殊启示。她这样做是 出于对普遍启示的一种错误认知,表现为人类经验主义(科学探究的基础),为的是验证或否定上帝的特殊启示,但是特殊启示不曾也永远不需要被人类认证。
创造完成时,“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亚当和夏娃与上帝有公义的交通,并且被赐予掌管上帝所造的一切的权柄(创1:26-30)。在罪进入世界之前,在地如在天的幸福生活等待着他们和他们后代。创世记 3:1-7记述了人类心智所经受的那次影响深远的毁灭性打击,并牵连到此后在这世上生活的每一个人。毫无疑问,在这一段历史性的经文中,撒旦对上帝和人类发动了战争,而战场正是夏娃的思想。最后,夏娃用上帝的真理(创2:17)换取了撒旦的谎言(创3:4-5),从此人类的思想就彻底不同了。
经验主义方法的原初形式实际上起源于创世记3章。当撒旦在夏娃心中播下了怀疑上帝真确性的种子之后(创3:4),夏娃的判断是,她要想鉴定上帝的对错,唯一的办法是用她自己的思维和感官来试验他。保罗在罗马书1:25中论到那些跟随夏娃和亚当走在属灵冒险道路上的人,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主。”
很快,夏娃基本上接受了撒旦的谎言,面临着重大决择。要么她可以不服从地选择吃,要么她可以顺从地选择克制。夏娃相信她自己就能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最好的选择;上帝的命令显然不再具有权威性。她觉得上帝的口头启示不再决定她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上帝的权威命令现在看来只是一个选则。在撒旦的影响下,现在突然出现了其他的选择。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3:6)。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第一次原始的实证研究和归纳推理的历史实践。在人类违抗上帝的首次行动中,夏娃决定对这棵树进行三次测试,看看上帝和撒旦谁是对的。
她进行了这样的测试,第一个是物理价值测试。她观察了这棵树,在检查时发现它的果实“好作食物”。它具有营养价值。这些可能是夏娃的想法:也许撒旦是对的。上帝不让我享受人生的所有乐趣,不让我吃园中所有的果子,也许他太苛刻了。
基于这种看似肯定的反应,她进行了第二次测试。夏娃发现那果实“悦人眼目”。它不仅对她的身体有营养上的好处,而且她还发现它有情感或审美价值。把这句话放到后现代语言环境中,她看着这棵树时的感觉很好。
夏娃仍不满足,她想研究彻底。也许她想,我要再向前走一步。接下来是最后的测试。她看了看,发现这棵树在“使人有智慧”这一方面也是有吸引力的,它有智能价值,可以使她像上帝一样聪明。
在夏娃的深思熟虑中,她看到并认为那棵树真的很好。它满足了她的躯体、审美和智力需求。她在头脑中得出结论,要么是上帝错了,要么是上帝撒了谎;撒旦的诡计成功地把她从上帝绝对而且信实的真理中引诱了出来。人类的思想将永远被摧毁。夏娃被骗了,就违背上帝的旨意,从树上摘下果子吃了。亚当很快也做了同样的事(创3:6)。
保罗这样总结夏娃灾难性的行为。“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林后11:3;参见提前2:14)。夏娃被撒旦的谎言诱惑了的思想和亚当明目张胆的不顺从,导致了他们灵魂的堕落,结果,所有在他们之后的人的灵魂都堕落了(罗马书5:12)。因此,人类的思想被罪所摧毁。人类的思想是如此无力,以致于人类再也不可能与上帝交通了,再也无力从神的角度看待和理解人生了。人类此刻与造物主上帝疏远了。
结果,上帝最初创造的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每一个后代都经历了与上帝和他的世界之关系的残酷反转。
1. 他们不再关心上帝的意念,只关心人的意念(诗53:1;罗1:25)。
2. 他们不再有属灵的视力,被撒但蒙蔽,以致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林后4:4)。
3. 他们不再是智慧人,乃是愚昧人(诗14:1;多3:3)。
4. 他们在上帝面前不再是活着的,乃是死在他们的罪中(罗8:5-11)。
5. 他们不再喜爱天上的事,只喜爱地上的事(西3:2)。
6. 他们不再行走在光明中,而是行走在黑暗中(约12:35-36,46)。
7. 他们将不再拥有永恒的生命,而是面对永恒的死亡——即永远与上帝分离(帖后1:9)。
8. 他们不再活在圣灵的国度里,而是活在肉体的境界里(罗8:1-5)。
休·罗斯似乎忽略了这场灾难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他坚持认为,人类从观察自然界所获得的知识(而不是启示)应该等于甚至优于上帝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他试图使人类的发现或理解等同于启示,而根据定义,启示只有通过上帝的揭示才能被准确地认知。[36]
事实上,圣经所定义的普遍启示,并不能揭示任何在《圣经》的特殊启示中找不到的东西。夏娃和休·罗斯博士都糊涂地用人类获得的知识来代替上帝的启示,代替他在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中恩典的预备。
恰当的释经学
国际圣经无误理事会(ICBI)经过多次会议,在其文献中传达了20世纪末福音派学者对恰当释经学的共识。[37] 以下摘录表明了他们对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结论。[38]
“第二十条 我们承认,既然上帝是所有真理的作者,因而所有真理,无论是圣经以内的还是圣经以外的,都是一致和连贯的,《圣经》在涉及到自然、历史或任何其他事物时都会说真理。我们进一步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圣经外的数据对于澄清圣经的教导及纠正错误的解释有价值。
我们否认,圣经外的观点曾经驳倒《圣经》的教导,或持有优先权。
这里所论及的与其说是真理的本质(在第六条中说明),不如说是真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是针对那些认为真理相悖或矛盾的观点。本条认为,合理的释经学会避免矛盾,因为上帝从不承认两个逻辑上相反的命题是真的。
然而,无论圣经以外的研究如何促进和澄清《圣经》,《圣经》教导的最终权威在于其本身,而不是在《圣经》之外的任何地方(除了上帝自己)。本条否认的目的是要表明上帝在圣经中的教导优于任何经外的知识。
第二十一条 我们承认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的和协性,因而圣经教导与自然界的事实也是和谐的。
我们否认任何真正的科学事实会与任何一段经文的真正含义相矛盾。
本条继续前一条的讨论,指出上帝的普遍启示(《圣经》以外的)和他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的一致性。所有人都承认,对《圣经》的某些解释和科学家的某些观点会相互矛盾。然而,这里坚持《圣经》的真理和科学的事实永远不会互相矛盾。
‘真正的’科学永远符合《圣经》。然而,基于自然主义预设的科学必然会与《圣经》的超自然真理发生冲突……”
虽然这些简短而有分量的陈述没有对论及的话题进行详细的探讨,也不一定与本章的每一个结论都一致,但这些陈述确实确立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1. 上帝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高于上帝在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
2. 上帝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解释上帝在自然界中的普遍启示,而不是相反。
ICBI结论的基础是用传统的、经过时间检验的、语法历史释经学方法来解释圣经。[39] 然而,当一个人致力于通过偏离历史语法的方法,下决心要让堕落罪恶的人凭着对这个被咒诅已败坏之受造界的有限观察而作出的解释,与《圣经》无误的命题式真理性陈述相吻合时,他实际上是使一种新的释经学替补上位,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让《圣经》与堕落、黑暗思想的见解协调起来,并把这种目的正当化。
恰当释经学的另一个方面几乎总是在关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讨论中缺失,那就是上帝的光照,即《圣经》向真正的基督信徒承诺从上面来的圣灵的帮助,教他们正确地解释《圣经》。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林前2:12-13)。
当人们对自己曾经的模糊认识有了新的理解时,通常用“我才恍然大悟”或“灵光乍现”来描述。上帝的灵就是这样帮助信徒理解《圣经》的。
我们学习经文的时候,可以献上一个很好的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119:18)。这句经文承认在理解《圣经》时对上帝光照的巨大需求。还有一句经文也是如此:“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诗119:33-34,另见第102节)。
上帝不仅要基督徒知道,而且要他们明白和顺服。所以他借着圣灵帮助他们。信徒,就像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和耶稣说话的那两个门徒,接受了上帝的帮助:“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45)。诗篇的作者也证实,上帝通过光照的事工使人明白圣经的意义(诗119:130)。
保罗和约翰也在《新约》中对此发表了评论。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1:18-19)。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一2:27)。
关于上帝光照的真理并不是说不需要有恩赐的人作教导(弗4:11-12、提后4:2),也不是说不需要下功夫认真研读《圣经》(提后2:15),但它确实应许我们,不必被教会的教条奴役,也不要被假教师误导。我们学习《圣经》的主要依靠应该是其作者——上帝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
1. 对于科学观察或对这些观察的解释,没有任何上帝光照的应许。
2. 对于普遍启示,没有上帝光照的应许。
3. 然而,对于《圣经》中的特殊启示,才有上帝光照的应许。
休·罗斯口头上说的是“扎实的解经”,但与他所说的相左的是,他采用了新的释经学,忽略了历史语法方法。[40] 当他把普遍启示的价值和级别等同于特殊启示的价值和级别时,要么否认了上帝对特殊启示特别应许的的光照,要么错误地假定上帝的光照也适用于普遍启示。
圣经的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人的预设、信念和价值观的集合,他从中尝试理解世界和人生。“世界观是一种概念模式,通过它,我们有意无意地将我们相信的一切安放其上或装进其中,并通过它来解释和判断现实。”[41] “世界观首先是对世界的解释,其次是在生活中的应用。”[42]
一个人如何形成世界观?从哪里开始?每一种世界观都是从预设开始的(即一个人假设为真、不用从别处或别的系统而来的独立证据支持的信念)。任何对现实的解释,无论是针对部分还是整体,都需要先设置解释的立场,因为宇宙中没有“中立”的思想。预设是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基础。
一个坚定地建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世界观包括哪些预设?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是20世纪后半叶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福音派神学敢于承认一个预设,而且只有一个:一个活着的、有位格的、可以通过他的启示而被认识的上帝。”[43] 没有模棱两可,亨利博士直截了当地、清楚地认定“我们的神学体系不是绝对可靠的,但上帝的命题性启示是绝对可靠的。”[44] 亨利早先曾阐述过这个主题:基督教在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作出预定时,其出发点是以经文为证的自我揭示的上帝,而不是根据解释者的意愿和创造性的猜想而自由修改的有神论。”[45] 罗纳德·纳什(Ronald Nash)以类似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人类和他们所居住的宇宙是在圣经中揭示自己的上帝创造的。”[46]
可以说,以下两个主要预设是本章所包含的思想的基础。第一是存在着一位永恒的、有位格的、超越的、三位一体的、造物主上帝。其次,《圣经》中的上帝在他特殊启示的绝对可靠无误的《圣经》中揭示了他的性格、目的和意志,《圣经》比任何其他来源的启示或人类推理都优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对待基督教护教学的态度会影响他对世界观的态度。[47] 一个恰当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应该循证性地通过人类的推理而建立护教体系的内容,然后转向特殊启示,还是预设性地从特殊启示开始?”[48] 循证主义者,如休·罗斯,从《圣经》以外的论据开始,试图证明《圣经》或更好地理解《圣经》,[49] 而预设主义者从《圣经》开始来了解世界。[50]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普遍启示的看法将极大地影响其护教系统。本章前面讲过,《圣经》中的特殊启示为自然界的普遍启示设定了界限,这一结论引导我们走向预设性护教。[51]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52] 本作者提出如下的实用性定义:
基督教世界观主要通过上帝特殊启示的镜片,即《圣经》,其次通过上帝在受造物中的、根据人类理性解释的、服从于《圣经》并与之一致的自然启示,来观察和理解造物主上帝和他的创造(即人和世界),为要信靠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从而用自己的意念和生命,从现在到永远都荣耀上帝。
基督教世界观与其他世界观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基督教世界观和其他的世界观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它1)承认上帝是所有真理的唯一来源,2)将所有的真理都联系到对上帝的理解以及他对我们今生和来世的旨意。亚瑟·福尔摩斯(Arthur Holmes)完美地总结了基督教世界观将绝对真理与上帝联系起来的独特含义:
1. 说真理是绝对而不是相对的,意味着真理是不变的,是普世相同的。
2. 真理的绝对性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因为追根溯源它来自那位永恒的上帝。真理的基础是上帝和他的创造的“形而上的客观性”。
3. 因此,绝对的命题性真理取决于上帝绝对的人格真理(即信实),人们可以相信他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53]
关于基督教世界观,特别是在基督徒中,有没有普遍的误解?有,至少有两个错误的概念。第一个错误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所有方面都与其他世界观不同。虽然这不是真的(例如,所有的世界观都接受万有引力定律),但基督教的世界观在最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和独特的,特别是涉及到上帝的属性、《圣经》的性质和价值、以及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排他性。第二个错误是《圣经》包含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常识应该把这种错误的想法排除在外。然而,《圣经》本身确实包含了基督徒属灵生命和敬虔所需要的一切,对独一真神的认识是最高和最重要的知识水平(彼后1:2-4)。此外,虽然《圣经》并没有详尽地涉及每一个领域,但当《圣经》在任何一个主题领域发言时,它都具有权威性。一个人对待基督教护教学和世界观的态度最终会影响他对学科整合的态度,即对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人类学习所获得的知识的综合和理解。[54] 当我们考虑知识来源的整合时,应该遵守三个重要的原则。
1. 虽然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但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被启示的真理,也不是所有声称是真理的陈述都是真的。
2. 启示的真理是确定的,而非启示的真理之主张往往是错误的、有待修正的。例如,创世记1-2章的内容是绝对确定的,因为它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而科学的起源理论最多只是尝试性的。
3. 启示的真理应该有助于解释非启示的真相/知识。例如,创世记1-2章里确定的内容应该用来验证或否定关于起源的尝试性科学理论。
这并不是要让神学家成为科学家,而是要用启示的真理作为判断非启示真理主张的基准。
然而,这应该可以防止科学家像休·罗斯那样毫无根据地篡夺神学家的角色。通过抬高基于对受造物研究的非启示性真理主张,将之提升到普遍启示的水平,他试图建立一种“双重的、可靠一致的启示”,[55] 这就把人类对被咒诅且败坏的受造物的解释,与上帝借《圣经》所赐的祝福和无误的启示,置于同等的地位。[56] 这样做,他便使错误地归于自然界普遍启示的非启示性的知识,等同于圣经中的特殊启示,有时甚至高于《圣经》中的特殊启示。因此,他用所谓的科学来解释《圣经》,并错误地声称圣经授权他这样做。
很不幸,休·罗斯的世界观在构建过程中并不总是符合圣经。他的护教方式是循证性的,而不是预设性的,他把非启示的、尝试性的知识与上帝所启示的确定性的真理统一起来,就好像它们是平等的一样。因为他这样做,他的思想和结论问题多多,所以他的渐进创造论观点也应该被拒绝。
关于这种错误,罗伯逊·麦克奎肯(J. Robertson McQuilken)在三十年前就发出过警告。虽然他的陈述是针对行为科学的,但对于自然科学也同样正确,也同样适用。
我的论点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对圣经权威的最大威胁是完全出于善意的行为科学家,他会在前门把守护栏,严防任何神学家针对《圣经》的默示性和权威性的攻击,但是与此同时,他自己却通过文化或心理学的解释将《圣经》的内容从后门私运出去。[57]
答案
不,自然界不是《圣经》的第67卷书!把一般性的知识获取等同于上帝的启示(普遍的或特殊的)是一种错误的夸大,结果是虚谎。把普遍启示扩展到特殊启示所规定的范围之外,是不符合圣经的,会导致神学谬误。
自然界不是圣经的第67卷书,原因有以下七个:
1. 这会违背《圣经》关于不可添加正典的警告。
2. 它明显夸大了圣经关于普遍启示的论述。
3. 它错误地将普遍启示提升到与特殊启示相同的权威级别。
4. 它错误地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性质等同起来。
5. 它没有考虑到堕落和人类在一般知识领域里的思维弱势。
6. 它背离了历史语法释经学的规范。
7. 它来源于有缺陷的世界观、护教学和认知整合方式。
因此,休·罗斯博士需要重新思考并放弃他对自然界作为《圣经》第67卷书的回答,他需要使自己的回答重新与《圣经》保持一致。如此,他会最终纠正自己的悲剧性错误,即为了支持古老地球理论而提倡的渐进起源观,古老地球论是与《创世记》记载背道而驰的。基督教学者、领袖、外行人和接受了休·罗斯博士渐进创造论观点的学生也应该摒弃这一不符合圣经的立场,转而相信《创世记》。
[1] John C. Whitcomb, The Early Earth, rev.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6).
[2] Henry M. Morris and John C. Whitcomb Jr., The Genesis Floo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7); John C. Whitcomb, The World that Perish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8).
[3] John C. Whitcomb Jr., Darius the Mede (Philadelphia, P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63); John C. Whitcomb, Esther: The Triumph of God’s Sovereignty (Chicago, IL: Moody, 1979); John C. Whitcomb, Daniel (Chicago, IL: Moody, 1985); John J. Davis and John C. Whitcomb,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Conquest to Exi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0).
[4] 休·罗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1973年),并担任“相信的理由”组织(www.Reasons.org)的主席,该组织致力于促进一种渐进式的起源观(跨越非常长的时间),以支持一种主要基于据称是无懈可击的科学研究的年老地球论。他的著作包括:The Fingerprint of God: Recen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Reveal the Unmistakable Identity of the Creator (Orange, CA: Promise Press, 1991)《上帝的指纹:最近的科学发现揭示了造物主的明确身份》;Creation and Time: A Biblical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n the Creation-Date Controversy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4)《创造与时间:关于创造日期争议的圣经和科学观点》;Beyond the Cosmos: What Recent Discoveries in Astronomy and Physics Reveal about the Nature of God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9);《宇宙之外:天文学和物理学揭示了上帝的本质》;The Genesis Question: Scientific Advances and the Accuracy of Genesis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2001)《创世问题:科学进步和创世的准确性》;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 How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of the Century Reveal God, 2nd ed.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2001)《造物主与宇宙: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如何揭示上帝》,第2版;A Matter of Days: Resolving a Creation Controversy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2004)《几天之内:解决创造争议》。
[5]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6. 他的书,特别是引用的句子出现的部分(第53-72页),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积极的评论包括Paul Copan,JETS 39 (1996): p. 307-308;Guillermo Gonzalez),PSCF 46(1994):p. 270. 其他人则持中立态度,如John A. Witmer,BibSac 153(1996):p. 493. 许多人一直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针对罗斯对《圣经》的解读,代表作品有Mark van Bebber and Paul S. Taylor, Creation and Time: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ive Creationist Hugh Ross, 2nd ed. (Gilbert, AZ: Eden, 1996); John MacArthur, The Battle for the Beginning (Nashville, TN: W Group, 2001) p. 60-62. Jonathan Sarfati, Refuting Compromise: A Biblical and Scientific Refutation of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Billions of Years), as Popularized by Astronomer Hugh Ross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反驳妥协》中译本见www.chinesecreationscience.org)其他文章可以在创世记问答(www.Answers in Genesis.org)和创造研究所(www.icr.org)的网站上找到。
[6]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55-58.
[7] 同上,第57页。
[8] 同上。
[9] 同上,第56-57页。
[10] 作者调查了超过25位解经家,其中没有一个人提示这节经文可能是指通过自然中的普遍启示来传福音。见Van Bebber在Creation and Time: A Report第37-39页中的扩展讨论。Douglas F. Kelly 在Creation and Change (Ross-shire, Great Britain: Christian Focus, 1997), 第230–31页, 注释49 and 50中,评论了罗斯在其他地方强解经文的做法。
[11]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6.
[12] 从自然界中,我们不会知道上帝被描绘成一个位格,一个男性,一个三位一体,一个唯一真正的上帝,拥有不可分享的属性(例如,他的荣耀和无所不知)和可分享的属性(例如,他的爱和恩典)。上帝的这些基本特征是通过《圣经》所揭示的,而不是通过自然界的普遍启示。相比之下,如果局限于自然的普遍启示所提供的内容,我们对上帝的知识会很贫乏。
[13] 瞥一眼罗马书10:9-13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4] 见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6-58. 他用“双重”来表达普遍与特殊启示的平等。
[15] Morris and Whitcomb, Genesis Flood, p. 458, n. l.
[16]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6.
[17] Richard L. Mayhue,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TMSJ 15 (Fall 2004): p. 227– 236.
[18] F.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VP, 1988); R. Laird Harris, Inspiration and Canonicity of the Bible, rev.e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69), p. 129–294; Bruce Metzger,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Oxford Press, 1987).
[19]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7.
[20] 这七处圣经文本都没有教导说历史是普遍启示的源头之一。相反,下列神学著作却将历史视为普遍启示的一部分: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6), p. 154–55; 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Minneapolis, MN: Bethany, 2002), p. 70–71; 及Renald Showers, “General Revelation,” part 1, Israel My Glory (August/September 1995): p. 22. 说历史不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并非否认《圣经》讲的是上帝之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为(参考伯12:23;但2:21,4:17)。然而,如果我们要清楚地知晓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只能从《圣经》的特殊启示来了解,人写的历史叙述不能看作是普遍启示的另一个来源。
[21] Robert L. Thomas,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The New Versus the Old (Grand Rapids, MI: Kregel, 2003) 在第5章“General Revelation and Biblical Hermeneutics”中提出了这一论点(第113–40页)。“任何扩大普遍启示范围的努力,使其包括关于受造界、人或除神以外其他任何方面的信息或理论,都没有《圣经》支持。《圣经》将普遍启示的范围限制在有关上帝的信息上”(p. 117)。
[22] James B. Jordan, Creation in Six Days: A Defense of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of Genesis One (Moscow, ID: Canon, 1999), p. 113–115. 作者将《诗篇》19篇的教导与那些希望将《诗篇》的意义扩展到科学探究领域之人的教导进行了比较。John Street, “Why Biblical Counseling and Not Psychology?” in John MacArthur, gen. ed., Think Biblically!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p. 214–219. 作者根据有关心理学的最新著作对《诗篇》19篇进行了研究。
[23] 见Stephen R. Spencer, “Is Natural Theology Biblical?” GTJ 9 (1988): p. 59–72.
[24] 同上。
[25] John D. Hannah, “Bibliotheca Sacra and Darwinism: An Analysi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GTJ 4 (1983): p. 37–58. “It behooves us to remember to be cautious not to neglect the exegesis of Scripture and the qualitative gulf between special and general revelation” (p. 58).
[26]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5–58.
[27] 本节改编自Richard L. Mayhue,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TMSJ 15 (Fall 2004): p. 227–236.
[28] The New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新牛津英语词典简编本),“authority”条目。
[29] Bernard Ramm, The Pattern of Religious Authorit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59), p. 10.
[30] BDAG,3rded. Rev.,见“ἐξουσία”条目。参见TDNT,“ἐξουσία”条目。
[31] John M. Frame, 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 formed, 1994), p. 127. 又见 Greg L. Bahnsen, “Inductivism, Inerrancy, and Presup- positionalism,” JETS 20 (December 1977): p. 289–305; John M. Frame, “Van Til and the Ligonier Apologetic,” WTJ 47 (1985): p. 279–299; Tim McConnel, “The Old Princeton Apologetics: Common Sense or Reformed?” JETS 46 (December 2003): p. 647–672.
[32]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7.
[33] 同上,第56页。
[34] 虽然已经有很多关于普遍启示的文章,但以下的材料更有帮助。G.C. Berkouwer, General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55); G.C. Berkouwer, “General and Special Divine Revelation,”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ed. by Carl F.H. Hen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58), p. 13–24; Bruce A. Demarest, General Revelation: Historical View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Gordon R. Lewis and Bruce A. Demarest, Integrative Theology, vol. 1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7), p. 61–82; James Leo Garrett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p. 43–91; N.H. Gootjes, “General Revelation in Its Relation to Special Revelation,” WTJ 51 (1989): p. 359–368;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4), p. 121–124; Spencer, “Natural Theology,” p. 59–72; Thomas,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p. 113–140.
[35]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5.
[36] 同上,第55-58页。
[37] 国际圣经无误理事会(ICBI)的学者在十年中(1977年至1987年)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议(1978年、1983年、1986年)和两次基督教团体大会(1982年、1987年),目的是系统阐述和传播圣经无误的真理
[38] Norman L. Geisler and J.I. Packer, Explaining Hermeneutics: A Commentary (Oakland, CA: ICBI, 1983), p. 15–16.
[39] Milton S.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 2nd ed. 1890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rpt. 1950), p. 173, 203–210.
[40]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8.
[41] Ronald H. Nash, Faith and Reas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8), p. 24.
[42] W. Gary Phillips and William E. Brown, Making Sense of Your World from a Biblical Viewpoint (Chicago, IL: Moody, 1991), p. 29.
[43] Carl F.H. Henry, 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vol. 1, God Who Speaks and Shows (Waco, TX: Word, 1976), p. 212.
[44] Carl F.H. Henry, “Fortune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View,” Trinity Journal 19 (1998): p. 168.
[45] 同上,第166页。
[46] Nash, Faith and Reason, p. 47. He gives the same answer in Worldviews in Conflic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2), p. 52.
[47] 本节的部分内容摘自本作者为麦克阿瑟总编的《按圣经思考!》(Think Biblically!)撰写的引言,第13-16页。
[48] Robert L. Reymond, The Justification of Knowledge (Philadelphia, P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6), p. 7–8. 又见Steven B. Cowan, ed., Five Views on Apologetic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0).
[49] 最近出版了一本支持这种方法著作:R.C. Sproul, John Gerstner, and Arthur Lindsley, Classical Apologetics: A Rational Defens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A Critique of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 更深入的评论请参阅George J. Zemek, “Classical Apologetics: A Rational Defense: A Review Article,” GTJ 7 (Spring 1986): p. 111–123.
[50] 见 Cornelius Van Til, Christian Apologetics, 2nd ed, William Edgar, ed. (Phillipsburg, NJ: P&R, 2003) 及 Stephen R. Spencer, “Fideism and Presuppositionalism,” GTJ 8 (Spring 1987): p. 89–99. 还可参考 John C. Whitcomb Jr., “Contemporary Apologetics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part 1, BibSac 134 (April–June 1977): p. 99–106 and The World that Perished, p. 95–139.
[51] 关于护教方法论的重要性,一个经典的历史例证与“伽利略事件”有关。参见Terry Mortenson,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Are They Related?”, TMSJ 15 (Spring 2004): p. 73–74.
[52] 有关基督教世界观简史和美国近期的属灵环境,见Carl F.H. Henry, “Fortune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View,” Trinity Journal 19 (1998): p. 163–176. 和Carl F.H. Henry, “The Vagrancy of the American Spirit” Faculty Dialogue 22 (Fall 1994): p. 5–18. 从历史上讲,詹姆斯·奥尔(James Orr)被公认是第一位以“世界观”为核心思想来组织基督教思想的现代神学家,见James Orr,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Edinburgh: A. Elliot, 1893; repri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48).
[53] Arthur F. Holmes,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7), p. 37.
[54] 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出色讨论和总结,见See Thomas,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p. 121–131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and summation of the issues. 也可以参考Spencer, “Natural Theology.”
[55]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56.
[56] 同上,第57页。
[57] J. Robertson McQuilken, “The Behavorial Science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JETS 20 (March 1977): p.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