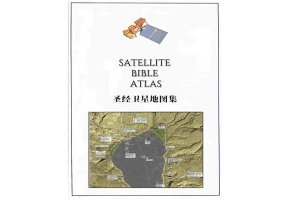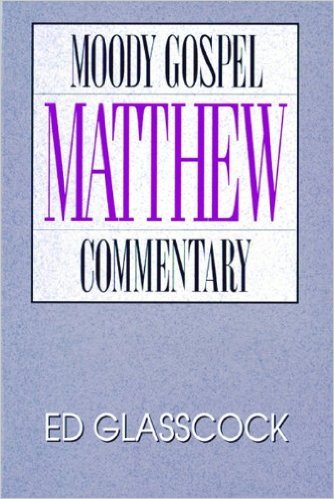第三章:“深度时间”与教会的妥协:历史背景
特里·莫滕森(Terry Mortenson)[1]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基督徒大学生,思考进化论及亿万年历史的问题时,魏德孔博士的著作《创世记大洪水》(The Genesis Flood)、《灭亡的世界》(The World That Perished)和《早期地球》(The Early Earth),对我帮助很大。他在《以斯帖记:上帝主权的胜利》(Esther : Triumph of God’s Sovereignty)一书中,对以斯帖记的精彩分析,使我受益匪浅。我在三一福音神学院读书时,通过电话认识了他,此后多次与他交往。几年前,我有幸在威斯康星州的创造论研讨会上,与他同为讲员。在与他的所有交往中,他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爱上帝,爱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话语,心系失丧者。他是过去半个世纪极少数坚决支持创世记第1-11章的真理性的神学家之一,这对我一直是极大的鼓励。我很高兴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并以此尊荣这位基督的忠实仆人。
引言
今天,不仅非基督徒认为地球和宇宙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而且大多数基督徒(包括基督徒领袖和学者)也都把这种说法当作科学事实来接受。但是,“深度时间”成为主流理念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被基督徒接受的过程,至关重要。
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前,我们需要记住使徒保罗的话。他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道: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著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3-5)。
保罗说,我们介入了一场大战——一场思想大战。“各样的计谋”和“自高之事”是与上帝的知识相悖的,也就是敌对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保罗在警告歌罗西的基督徒时,向我们介绍了更多这些敌对圣经的思想:“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2:8)。保罗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他知道,基督徒非常可能被错误的观念引入歧途。他警告提摩太时,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提前6:20-21)。来自文化的社会压力也很危险。在加拉太书2:11-14中,保罗描述了彼得因惧怕人而陷入虚伪,并且扭曲福音。
当我们追溯这种亿万年历史观的由来时,我们看见它是臆想的产物,是基于敌对圣经的哲学假设。我们还看见,许多良善且真诚的基督教领袖和学者被这种观点所束缚,以至于在过去的200年间,该观点被教会广泛接受,结果导致许多基督徒偏离信仰,甚至完全迷失。
“深度时间”的起源
地质学作为一个单独的科学领域,只有约200年的历史。地质学包括系统性的现场研究、岩石和化石的收集与分类、以及对形成这些岩石层和化石的历史事件进行理论重塑。
在这之前,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已经注意到岩石中的化石。很多人认为化石是古生物的遗骸变成的石头,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包括特土良、约翰金口和奥古斯丁)将其归因于挪亚大洪水。但其他人拒绝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石是自然界的恶作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赋予生命的岩石,或者是上帝的创造,或者甚至是撒旦的诡计。直到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通过显微镜对化石木材的分析证实,化石是矿化的生物遗骸,辩论最终尘埃落地。
1750年之前最重要的地质思想家之一是尼尔斯·斯滕森(Niels Steensen,1638-1686年),他是荷兰解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他的地质著作《关于固体中天然含有的固体的先驱论文》(The Prodromus to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Solids Naturally Contained within Solids,发表于1669年)中,他提出了今天广为接受的叠加原理。叠加原理认为沉积层是以连续的、基本上水平的方式沉积而成的。因此,较低的地层沉积于其上面的地层之前(因此更古老一些)。他相信地球约有6000年历史,[2] 并且相信全球性的挪亚大洪水沉积形成了大多数含化石的沉积岩层。
随后的一个世纪,英国地质学家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1665-1722)、亚历山大·卡科特(Alexander Catcott,1725-1779)和德国地质学家约翰·莱曼(Johann Lehmann,1719-1767)等人出版了一些书,强化了年轻的地球和全球性洪水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教会在前18个世纪的信仰一致,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述。[3]
18世纪后半叶,一些英国和欧洲的地质学家将岩石的形成归因于漫长时间的地质过程,而不是挪亚大洪水。几位有名的法国科学家也支持亿万年的观点。广受尊敬的科学家孔德·德·布封(Comte de Buffon,1707-1788年)认为地球的历史受自然法则支配。因此,他坚决拒绝《圣经》记载的挪亚大洪水。在他的《自然史》(Epochs of Nature ,1779年)中,他想象地球曾经像是一个熔化的热球(是从太阳上撕裂下来的),经过七个时期的冷却,用了大约75000年(他未出版的手稿说约3百万年)的时间,达到现在的状态。他还认为,通过对具有“水性、油性和延展性”的物质加热,第一个生物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4]
天文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Pierre Laplace,1749-1827)在其著作《宇宙体系的阐明》(Exposi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Universe,1796年)中提出了“星云假说”。该理论认为,太阳系曾经是炙热旋转的气体云,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冷却凝结成行星。尽管这种推测性假设没有任何观察或实验数据的支持,并且被当时大多数科学家所拒绝,现今却作为大爆炸宇宙论的一部分,成为主流的观点。1809年,贝壳类动物学专家冉·拉马克(Jean Lamarck)在他的《动物学哲学》(Philosophy of Zoology)中提出了漫长时期的生物进化的假说。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包括非基督徒科学家)都拒绝进化论的观点,但这一假说却为达尔文1859年的名著《物种起源》铺平了道路。拉马克想象出的进化机理(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早就被证明是错谬的。
19世纪初,地质学开始发展成一个学科领域,新的地质学理论得到推崇。亚伯拉罕·维尔纳(Abraham Werner,1749-1817)是德国有名的矿物学教授。遗憾的是,正如一位相信进化论的地质历史学家所说,“维尔纳倾心于传授教条主义理论和推测,根本不考虑事实,也极少考虑可证实的原理。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基本上以假设为基础的观点。”[5] 在维尔纳的28页矿物学著作《各种岩石的简短分类和描述》(Short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Rocks,1786年)中,他根据对自己家附近的沉积岩的研究,用一小段文字,阐述了他的地球历史论。他推测,地球的大部分地壳,是由一个缓慢收缩的全球性海洋,经过大约一百万年的时间,化学地或机械地沉淀而成的。这是一个简单漂亮的理论,但维尔纳忽略了岩石中的化石。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化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关沉积的时间、沉积速度和石化速度的信息。维尔纳是一位充满活力且广受欢迎的教师,19世纪许多最伟大的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尽管他的简单化理论很快就被抛弃,但他的漫长地球史观一直云绕着他的学生们。[6]
同时在苏格兰,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正在发展另一套地球历史理论。他在大学期间学习医学,学完以后接管家庭农场一段时间,但他的真爱是地球研究。1785年,他发表了一篇期刊文章,1795年又出版了一本书,标题均为《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他想象,各大洲经过长时间的侵蚀而慢慢融入海洋,这些沉积物接受地球内部的热量而逐渐变硬,然后扭曲抬升,成为新的陆地。新的陆地最终又被冲蚀汇入海洋中,变硬并升高。因此,在他看来,地球史是周期性的。在一份被许多同时代者指控为无神论的著名声明中,他说他找不到岩石有开端的证据,这使地球历史变得无限长。他也极少关注岩石中的化石。
灾变论与均变论之争
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8- 1832年)是一位非常关注化石的学者,他是法国著名的比较解剖学家和古脊椎动物学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他提出了关于地球历史的灾变论。他在1813年的《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7] 居维叶认为,在未知的漫长的地球历史时期中,许多区域性或近乎全球性的灾难性洪水摧毁了各种生物,并且把它们掩埋在沉积物中,其中一些变成化石被保存下来。居维叶说,多数灾难都发生在人类受造之前,只有一次例外。他坚决反对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上帝在地球历史的不同时期超自然地创造了不同的生物。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769-1839)是一位排水工程师兼测量师。他在英国各地工作时,迷上了地层和化石。像居维叶一样,他拒绝生物进化的理论,但对地球历史秉持古老地球灾变论。在1815年至1817年间出版的三本著作里,史密斯展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第一张地质图,并解释了根据特征性(指标)化石而推定的岩层形成的顺序和相对年代。[8] 他被称为“英国地层学之父”,因为他发明了依据岩石层中的化石,来决定岩石层形成的相对时期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被进化论地质学家使用。[9]
这里需要提及另外两名灾变论学者,因为他们对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1784-1856年),牛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也是1820年代英国地质学界的领军人物。最初,他遵循居维叶和史密斯的灾变论观点。像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巴克兰是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他的两个学生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和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在1830年代以后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均变论地质学家。巴克兰在他的《地质证明》(Vindiciae Geologicae,1820年)中指出,地质学与创世记是一致的。地质学通过提供创造和上帝持续维护大自然的证据来证实宗教,并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全球性的挪亚大洪灾的发生。然而,巴克兰认为,洪水的地质证据仅存在于表层的沙质和砾石构造以及各大陆的地形特征中。他相信数千英尺的沉积岩层(如我们在大峡谷中所见)比大洪水早了不知多少千年。为了使他的观点与创世记保持一致,他考虑了长日论的可能性,但更喜欢间隔理论,二者都是在180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完全没有分析创世记的经文,没有探究古老地球理论怎么可能与圣经经文相调和。他只是引用其他地质学家或神学家作为权威依据。与居维叶一样,他相信超自然的多次创造,人类的创造只有几千年。
三年后,巴克兰发表了流传甚广的《洪水残骸》(Reliquiae Diluvianae,1823),他认为该书为大洪水提供了进一步的辩护(尽管洪水的地质效应有限)。当他讨论表面地质特征时,他还是没有深入研读圣经中有关大洪水的经文。从巴克兰在1820年代的个人信件中明显可以看出,在他的头脑里,在重塑地球历史方面,地质证据比圣经经文证据更有质量和可靠性,因为书面记录容易受骗或出错,而岩石是真实的且不能被人改变。[10] 虽然他没有断言圣经有误,但是他的这种推理绝对隐含着这层意思。
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785-1873)是巴克兰在剑桥大学的同行,1818年曾任地质系主任。当时他承认自己对地质学几乎一无所知,但他领悟力很强。他也曾是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一生都认定古老地球理论与圣经不矛盾。但是,无论在他最初几年相信灾变论的时候,还是后来持定均变论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尝试表明地质理论与创世记第1-11章的经文是怎么调和的。[11]
人们甚至不清楚他是否持守间隔理论,对挪亚洪水不知他是认同局部洪水还是平静洪水观点。应该指出的是,当查尔斯·达尔文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时,塞奇威克帮助他建立了古老地球思想。之后,达尔文用这些敌对圣经的思维模式,轻而易举地发展出他的缓慢渐进的生物进化论。
当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1845年发表了一种进化理论时,塞奇威克在一篇长达85页的评论文章中严厉反驳钱伯斯的观点,称其为“怪异的错觉”,受到了“错谬哲学的蛇套”影响。[12]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1859年)出版后不久,在1865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塞奇威克与其他616人签署并公布了一份声明。签署人对达尔文的理论“质疑圣经的真理性和权威性”表示关切。[13] 这位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兼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通过倡导古老地球地质学理论诋毁了圣经的权柄,为达尔文通过生物进化论进一步诋毁圣经铺平了道路,结果令他自己都感到沮丧。
在巴克兰和塞奇威克等人的影响下,1820年代,大多数地质学家以及许多英国和北美的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广泛地接受了古老地球灾变(有时也称为“洪水”)地质学理论。
1830年至1833年,灾变论遭遇致命的一击,巴克兰曾经的学生、律师查尔斯·莱尔(1797-1875)发表了三卷颇有影响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为了复兴及补充赫顿的思想,莱尔的《地质学原理》提出了他认为地质学解释应该遵循的原则。他的理论是激进的均变论,他坚持认为,只能用现在地质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来解释过去的地质活动。换句话说,在整个地球历史上,地质的变化都是匀速的。莱尔坚信,从未发生过大陆范围或全球范围的灾难性的大洪水。
莱尔的工作导致巴克兰于1830年代初抛弃了对地质证据的洪水灾变论的解释。1836年,巴克兰在他著名的两卷关于地质学的《布里奇沃特论》(Bridgewater Treatise)中公开了他的思想转变,他在其中一个段落和另一个简短的脚注中,将圣经中的大洪水描述为平静的、没有地质学意义的。[14] 1831年,塞奇威克公开地收回了自己的灾变论观点,并接受了莱尔的均变论。
在摧毁人们对创世记大洪水和圣经时间表的信心方面,莱尔常常被给予太多的关注。可是,在莱尔发表他的著作之前,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地质学家和神学家,已经在破坏圣经的教导。灾变论已经大大削弱了挪亚洪水的地质意义,延伸了地球的历史,使之远超过传统的圣经历史观。莱尔的工作只是对相信大洪水的最后一击。他通过用缓慢渐进的过程解释岩石的形成,彻底抹杀了大洪水对地质的影响。虽然到了1830年代后期,灾变论者已经为数不多了,但是灾变论并没有立即消失,他们也相信挪亚洪水在地质学上的意义微不足道。
到了19世纪末,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地球的年龄有数亿年。1903年同位素测年法问世,20世纪期间,地球的年龄被扩展到45亿年。
假设、观察和解释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古老地球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后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并不是建立在“让事实说话”的根基上。理解观察与解释之间的区别以及理解哲学/宗教的前提假设对于地质学的巨大影响,至关重要。属于哲学和宗教范畴的前提假设,对于观察的过程、收集哪些数据、向科学界报告哪些数据、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数据,影响巨大。
“深度时间”的构建者并不是客观无偏见地追求真理,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人。科学工作者的学术培训,常常使他们对属于哲学范畴的非科学性的前提假设视而不见。而这些前提假设直接影响到他们观察什么以及对观察的解释,影响到他们做哪些实验及探索哪些问题,影响到会考虑哪些可能性的结论。针对19世纪初期的地质学,一位颇受尊敬的科学历史学家指出:
“最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科学家们构建(岩层)分类时,他们显然将自然界放进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框架里。他们以前的经验和培训、对机构的忠诚、以及科学家的个性和观点,都对设定框架的‘自然’边界有影响。”[15]
其它因素也可能会扭曲科学家们的想法及其发表的结果:同行的压力、贪婪、嫉妒、对金钱或声誉的热爱等,这些可导致蒙骗和欺诈。而这种欺骗,科学界可能长期浑然不知。[16] 当然,这些因素并非对所有的科学家都有同样程度的影响。此外,人的理论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他的宗教世界观,包括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世界观对古老地球地质学起源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认知。人的世界观不仅影响他对事实的解释,也影响他对事实的观察。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作出了正确的评论,他说:“人一般能明察他们期望看到的,却忽视他们不期望看到的”。[17] 1830年代后期,针对英国地质学界对泥盆纪形成的争议,地质历史学领袖马丁·鲁德威克(Martin Rudwick)提出了启发性的阐述。他写道:
“此外,大多数与泥盆纪争议有关的实地观察记录,不仅仅是‘充满了理论’,这一点是大多数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现在都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而且也 ‘充满了争议’ 。具体的观察目标和现场观察的次序,通常明显地旨在寻找某一方面的经验证据,这些证据不仅要与争议有关,而且也要有说服性。很多最中立的‘事实’观察,如果放在其大背景中,也可以看出是有意寻找、选择并记录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观察者己方的的解释,并贬损对方解释的合理性。”[18]
莱尔隐蔽地宣传斯克鲁普(George Scrope)用均变论对法国中部地质形成的的解释。1827年,莱尔这样说:“几乎没必要提醒读者,那些要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人,会轻易忽视跟他们的观点相抵触的事实,在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的情况下,只注意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19] 从那时至今,许多地质学家评价莱尔说,在他自己对地质学的解释上,莱尔对这一点也是视而不见。
可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观对地质现象的观察、选择及解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是19世纪初,地质学还处于萌芽阶段,个人和集体的地质学知识非常有限。正如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
“科学哲学家们已反复证明,对于任何一组数据,总是可以用多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科学史也证明这一观点,尤其是在一个新的范式的早期阶段,发明替代的解释方式并不困难。”[20]
1800年代初,古老地球论的发展是由哲学假设推动的。两个关键的假设是:(1)物质宇宙中的万物能够而且必须用时间、机遇、及作用于物质上的自然规律来解释;(2)自然界的物理过程,一直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运行方式、速度和强度在运行。这两个假设构成了均变论自然主义哲学的基础,后者于19世纪初控制了现代科学,比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早了几十年。虽然当今许多科学家在其地球历史模型中容许偶发性的大灾难,但均变论思维仍然根深蒂固,自然主义仍然掌权。因此,关于地球年龄以及如何正确解释地质记录的争论,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世界观冲突。
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老地球倡导者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自然主义均变论世界观。例如,布封写道:
“为了判断曾经发生了什么,甚至将要发生什么,只需检查正在发生什么。每天发生的事件、连续不断的重复运动、恒定的恒常重复的运作,这就是我们的起因和我们的逻辑。” [21]
布封还曾论证:
“我们必须从地球现在的面目出发,检查其不同部分的细节,从目前存在的现象通过归纳而判断其未来。如果一些因素仅仅偶尔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总是突然的和剧烈的,我们就不应该受其左右。这些因素在自然界的常规过程中没有地位。只有那些均一重复的运作、接踵而至没有间断的运动,才应该成为我们推理的基础。”[22]
赫顿也留下类似的文字:“必须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正在发生的地质变化,来解释地球过去的历史……除了地球上自然发生的力量,除了我们了解其原理的作用,其它的因素都是不容许的。”[23] 赫顿基于“以现在推测过去”的思维方式,否定了全球性大洪水的提法,他说:“确实,普世性洪水在地球理论中没有一席之地; 因为地球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系动植物的生命,而不是毁灭它们。”[24] 当然,现今的地球确实维系动植物的生存,而且今天没有全球性的大洪水。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从未发生过全球性大洪水。
显然,这些人通过坚称地质学家只能根据现在所知的自然过程来思考,那就先验性地(在观察岩石和化石之前)排除了创世记所记载的上帝在六日之内超自然的创世,并以超自然的方式引发了全球范围上长达一年的灾难性的挪亚大洪水。维尔纳、拉普拉斯、史密斯、莱尔和其他古老地球论的开拓者都遵循了同样的自然主义均变论推理。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地质学家(如英国的巴克兰和塞奇威克,美国的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和爱德华·希区柯克[Edward Hitchcock]),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自己却浑然不觉。
虽然有大量的地质证据表明圣经记载的有关创造、大洪水和地球年龄的教导,但因为上面所述的原因,古老地球的倡导者们无视这些地质证据。同样地,在过去200年内,所有被教导这些预设的地质学学生也都看不见与创世记相符合的大量证据。普罗大众对这些预设浑然不知,很容易地就被地质学家们借着媒体、博物馆、国家公园的标示牌、教科书以及电视里的科学节目所误导,接受了亿万年的历史。
地质学家们敌对圣经的态度
古老地球论的开路先锋们所秉持的偏见,并不完全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欧洲文化虽然名义上是基督教,但是很多人有意识地离弃圣经真理(至少创世记那部分),这种社会背景也为自然主义(不管是有神论或无神论)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温床。在诸多发表的文献中,作者们故意遮掩他们敌对圣经的世界观,他们嘴上说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来自同一群人的未发表的文字却常常暴露真情。布封意识到他的古老地球论不会被天主教教会接纳,他在未发表的手稿中估计地球的寿命为3百万年,但他出版的书却只给出75000年的地球年龄(这也同样让天主教的神学家不悦)。二十世纪法国科学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雅克·罗杰(Jacques Roger)说:“布封率先开创了独立自主的科学,不受任何神学的影响。”[25] 当然,有识辩力的基督徒会看到,布封并没有创立独立自主的科学,而是企图用自己不合圣经的神学主宰科学。他的科学只是挣脱了基督教的框架,但正是基督教的框架孕育了现代科学,并为世界赋予了意义。
居维叶对圣经真理的敌对更为隐蔽。在他的《地球理论》中,他略微提到了创世记、创造、大洪水和上帝,却排斥了早先人们从创造和洪水的角度去审视地质记录的工作。他不曾尝试将其理论与圣经记载的历史相调和,只是提到洪水后的圣经年代表为洪水提供了合理的日期。他没有具体提到任何经文,并无视创世记第1-9章和出埃及记20:8-11。
均变论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1832年在伦敦国王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解释说:
“一位杰出的作家和熟练的地质学家的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为了(神的)启示,也为了科学,为了任何形式的真理,应该像圣经不存在那样探究地质的物理部分。’”[26]
如果圣经没有描述与地球岩石的形成有关的任何事件(例如创造周和大洪水),这种推理可能是允许的。但是由于圣经确实讲到了此类事件,莱尔的办法就像试图通过研究幸存的纪念碑、建筑物、艺术品和硬币来写古罗马历史,却故意无视可靠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结果自然是不很准确。
几年之前,莱尔就私下透露了他对圣经的憎恨,以及他破坏圣经教导的阴谋。1829年8月11日莱尔写信给他的朋友,就是同样秉持古老地球均变论的地质学家罗德里克·默奇森,这是在他的《地质学原理》(1830)第一卷出版前几个月,在私信中莱尔透露说:
“我相信我对地质学进展的介绍将广受欢迎。老弗莱明(指约翰·弗莱明牧师)感到恐惧,他认为时代不会容忍我敌对摩西的论调,至少这个主题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欢迎,而且会让神职人员感到不适,但我才不怕。我将全力以赴,但要尽量以平和的方式。”[27]
大约在同一时间,莱尔与他的朋友乔治·斯克鲁普(另一位古老地球地质学家,英国国会议员)通信,他说:“如果能够在不冒犯人的情况下抛弃摩西的地质学,那将是历史伟绩。”[28] 为什么莱尔要让地质学离弃(神启示的)关于大洪水的准确的历史记录? 因为他是上帝一位论(Unitarian)或自然神论的信奉者,反叛了他的造物主耶稣基督,他希望地质学能够在自然主义预设下运作。1830年6月14日莱尔再次写信给斯克鲁普时,流露出更多的想法,他写道:
“我相信你可能会加入《季度评论》(Q.R.),这个平台会将(地质)科学从摩西手里解放出来。如果得到严肃的看待,(教会)方面对此已经准备好了。巴克兰说有一位主教(我们想可能是萨姆纳[John Sumner]),在《英国评论和神学综述》(British Critic and Theological Review)中对乌雷(Andrew Ure)[29]大为光火。他们终于看到摩西体系给他们带来的难堪和尴尬……(万物)或许有一个开端——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值得神学家们考虑——也许会有一个终结。就像你说的,物种有始也有终,但这个类比既脆弱又不贴切。也许这不过是一个类比,但我想说,也如赫顿所说的,‘没有开端的迹象,也没有终结的预期’……我的诉求只是,对于过去任何特定的时期,当有人用‘开端’作为避难所来困扰我们的时候,不要停止探究。所谓‘起始’,在我看来都是‘另一种自然状态’。如果你指出我是在否认‘开端’的证据,而不是否认‘开端’的可能性,你对我的攻击就不会有任何伤害。我害怕点破窗纸,就像你害怕在《季度评论》里谈摩西一样。也许我应该对《古兰经》更加温和一点,最好不惹它。我担心会刺激谁(尽管仅仅是历史方面)。如果我们不激惹,就会带动所有的人。如果你不趾高气扬,而是夸赞当今时代的自由和坦诚,主教和开明的圣徒们将与我们一起鄙视古今的物理神学家们。现在是进攻的好机会,庆贺吧! 《季度评论》居然向像你这样的罪人打开大门。
还有,五六年前(1824-25)我萌发了这个想法,如果能够在不冒犯人的情况下抛弃摩西的地质学,那将是历史伟绩。您必须提炼我的话,这样你才能尽量少说自己的话。让他们去感受吧,让他们去点破吧。”[30]
波特(Porter)通过对莱尔手稿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莱尔将自己视为“地质学的精神救主,他要把科学从摩西的旧时代中解放出来。”[31] 在幕后,许多早期地质学家谋划着如何破坏人们对圣经的信仰,尤其是对创世记第1-11章所记载的历史的信心,而且要说服教会,圣经的教导与地球的年龄和地球历史这个问题没有关系。这些地质学家极其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但是,当我们考察那些对古老地球论的发展举足轻重之人的神学取向时,这一切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布封是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者,他偶尔提一下上帝以掩盖他不是基督徒的事实。[32] 拉普拉斯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33] 拉马克是自然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骑墙派。[34] 维尔纳是自然神论[35]或可能是无神论者[36],因此“觉得无需将他的理论与圣经调和。”[37] 史学家对赫顿也是同样的结论。[38] 威廉·史密斯是一位模糊的自然神论者,但据他的外甥(一位地质学家)说,他绝对不是基督徒。[39] 居维叶名义上是一位路德宗基督徒,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他实际上是一个不虔诚的自然神论者。[40] 莱尔可能是自然神论者(或上帝一位论者,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41] 1820和1830年代地质学界的其他领军人物也同样是反基督教的。所以这些人绝不是客观的、无偏见的真理追求者,尽管他们希望当时的人如此评价他们,就像现代进化论者和许多科学史家希望我们如此评价他们一样。进化论古生物学者菲利普·金格里奇(Philip Gingerich)坦率地承认:“科学源于人们对世界本质的哲学性的探索,它窃取了一些从前蕴含在宗教中的奥秘。”[42]
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柯林斯(C. John Collins)为了捍卫他的古老地球观,在简短讨论了地质学之后陈述了以下谬论:
“首先,现代地质学的确不依赖于圣经——其实说现代地质学无视圣经也不对,因为很多地质学著作都引用了詹姆斯·乌雪的世界年代表,但这远不等于说现代地质学一开始就与圣经作对。实际上,19世纪初期,英国大多数地质学先驱都是虔诚的英格兰教会信徒,有些甚至是神职人员。只有在我们确定圣经要求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很年轻的情况下,说地质学敌对圣经才是正确的,但早期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圣经为其他可能的解释留下了余地。”[43]
这种说法是相当误导人的。那些现代地质学书籍鲜有提及《圣经》或乌雪,提及时也只是隐晦的或公然的嘲弄,他们绝不会把圣经的教导或乌雪的年代表放在眼里。此外,十九世纪初的神职地质学家(如英格兰教会的威廉·巴克兰、亚当·塞奇威克和威廉·科尼比尔[William Conybeare])倡导亿万年的地球历史,但他们从未提供圣经经文依据来证明他们对地球历史的看法与圣经一致。他们只是以自己为权柄,断言说古老地球论与圣经没有冲突。[44] 他们可能在道德生活、教会出勤率以及对基督是救主的信念上是虔诚的,但对于上帝在创世记中的话语,他们不虔诚,甚至是无视。
柯林斯在简要讨论了史蒂夫·奥斯汀博士(Steve Austin,年轻地球创造论地质学家)和达勒姆普尔(G. Brent Dalrymple,进化论地质学领袖)在同位素测年法上的工作后,如此总结他关于地质学的简短论述:
“双方都有很多技术细节(关于同位素测年法和地球年龄的问题),对这些我不懂得如何评估,也不想装懂。但是,我胸有成竹地说,对持观点迥异的人,达勒姆普尔是公平的,[45] 他读了奥斯汀的资料,并参照对技术作品的合理标准,对其进行了评估。他发现奥斯汀的材料不够格,不达标。因此,在我看来,奥斯汀质疑同位素测年法的声称,实在没有份量。最后,我总结,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地质学家的标准理论,包括他们对地球年龄的估计。据我所知,他们可能是错的。但如果他们错了,也不是因为他们把哲学假设掺进了他们的科学工作。”[46]
正如我们所见,柯林斯严重误判了哲学假设对地质学的影响力。柯林斯就他所知,承认地质学家可能错误地估算地球的年龄,这并不令人困惑。然而,虽然柯林斯承认自己没有技术资格评估古老地球地质理论,他却欣然让那些理论影响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并拒绝了相信圣经的创造论地质学家提出的论证,而这些论证指明了那些地质理论的错误以及错误的理由。可悲的是,一位自称没学过地质学及地质学历史的优秀旧约神学家,却告诉基督徒们,相信年轻地球创造论的地质学博士的论证,无足轻重。
基督教对古老地球地质学的回应
19世纪上半叶,教会以各种方式对灾变论者和均变论者的古老地球理论做出了回应。英国有一些作者(美国也有少数),成为“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他们提出了反对古老地球论的圣经、地质学以及哲学方面的论证。他们中有些是科学家,有些是神职人员,还有些既是按立的牧师,又在科学上训练有素,这种人才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通过阅读以及通过对岩石和化石的仔细观察,他们中许多人按照当时的标准具备了非常强的地质学评判能力。他们认为圣经记载的创世和挪亚大洪水对岩石记录的解释,远胜于古老地球论的解释。[47] 其他的基督徒在1800年代初期迅速接受了亿万年地球历史的说法,并试图将古老地球的长历史糅合进创世记,即使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仍处于摇篮期,而且均变论和灾变论仍在争辩中。
1804年,长老会年轻的牧师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年)开始教导基督徒应该接受亿万年的历史。他断言:“摩西的著述不能解决地球古老的问题。如果说摩西的著述解决了任何问题的话,它只说明了(人类)物种的古老。”[48] 1814年,他写了一篇评论居维叶《地球理论》的文章,他提出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塞进创世记1:1和1:2之间。[49] 那时候,查默斯已成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因此,这种“间隔理论”变得非常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查默斯是一位牧师,但他直到1811年才真正相信基督而重生得救,也就是说,他接受亿万年历史观之后七年,才重生得救。[50] 他信主以后也从未质疑古老地球的历史观。
1823年,一位受人尊敬的英格兰教会福音派神学家乔治·斯坦利·法伯(George Stanley Faber,1773-1854)成为长日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所谓“长日”,就是说上帝六日创造的“日”,并非字面意义,而是象征性的,指很长的时期 。[51] 因为受一本过时的地质学书籍的影响,法伯错以为古老地球论地质学家们所展示的化石的次序,“以最奇怪的方式验证了”创世记第一章中创造事件的次序。[52] 法伯的观点表明,他对圣经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古老地球论的牵制。他承认教会在历史上相信全球性大洪水,但他根据地质学而拒绝全球性大洪水的观点,并接受居维叶关于地球历史的灾变论观点。[53] 他毫无逻辑地指出,由于上帝歇息了他创造的工作,因此,创造周的第七天尚未结束。他说:“第七天实际上是对应着宇宙被造以后存在的时间。”[54]
为了接受地质学家们提出的地质年代,基督徒们还必须重新解释创世记第6-9章中有关大洪水的记载。我们已经提到了巴克兰和塞奇威克等灾变论学者。1826年,长老会牧师约翰·弗莱明(John Fleming,1785-1857)在一篇文章中反驳巴克兰等人。他认为挪亚大洪水是平缓的,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地质证据。[55] 弗莱明在否认大洪水的灾难性时,丝毫没有提及创世记对大洪水的细节描写。当时,这种“平缓大洪水”的观点,并不像公理会神学家约翰·派伊·史密斯(John Pye Smith,1774-1851)的局部性洪水观点那么流行。史密斯论证洪水只是美索不达米亚山谷(今伊拉克)中的局部性洪水。[56] 1830年代后期,莱尔的均变论获胜后,那些仍然相信大洪水是灾难性的人,接受了局部性洪水的观点。上面所有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同挪亚大洪水与解释数千英尺的沉积岩层的起源没有关系。
1800年代初期在欧洲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派神学,到了1820年代就开始侵入英国和北美。自由派认为创世记第1-11章与古巴比伦、苏美尔和埃及的创造和洪水神话一样,在关于历史的记载上,是不可靠和不科学的,因此对了解地质学毫无用处。
尽管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对创世记的各种古老地球论的解释仍然盛行,以至于到1845年左右,有关创世记的所有释经著作都抛弃了圣经年代和全球性大洪水。[57]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时(1859),年轻地球观在教会里基本上消失了。从那时起,大多数保守派基督教领袖和教会学者都把亿万年的地球年龄当作被科学证明的事实接受了,并坚持认为地球的年龄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许多敬虔的人也很快接受了进化论。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仅举数例。
浸信会的“讲道王子”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1834-1892年)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古老地球地质论(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地质学家说的是亿万年)。1855年,他在讲道中说:
“谁能告诉我起初是什么时候? 多年前,我们以为世界是以亚当的出现开始的。但我们发现,在亚当出现之前的数千年,上帝就在混乱的物质上做工,使其适合人类居住。上帝在造人之前,先在地上安放各种生物,这些生物会死,并留下上帝精湛技艺的痕迹。”[58]
在司布真一生的讲道生涯中,他没有持续地关注进化论和地球年龄,也从未说明如何释经才能让漫长的年代融入圣经。他的几处简短的陈述,表明他反对达尔文式的进化论,称其为谎言。[59] 然而,在1876年,他把人类被造之前已有亿万年历史的假设当作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60]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长老会神学家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1797-1878年)在其著作《什么是达尔文主义》(What is Darwinism ?,1874年出版)中强烈反对进化论。他认为这是无神论。然而,他却安然接受亿万年的历史。他早期倾向于间隔论,但在1860年后提倡长日论。他断言,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地球或人类的年龄。[61] 就像他的父亲A. A. 霍奇(A. A. Hodge ,1823-1886)一样,查尔斯·霍奇接受深度时间观,但比他父亲走得更远,他认为也许上帝用进化来创造万物。[62] 他还总结说,圣经中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亚伯拉罕时代。[63]
霍奇之后,沃菲尔德(B. B. Warfield,1851-1921)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首席神学家。沃菲尔德在学生时代是一位热情的进化论拥护者。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对进化论的观点摇摆不定,难以捉摸。负责编辑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的编辑们称他为“保守的进化论者”。[64] 鉴于他认为亚当和夏娃的身体可能是自然过程产生的(当然,在上帝的旨意下)[65],他被标签为“神导进化论者”。[66] 至于深度时间论,他不接受地质学家最长的时间估算,但相信有数百万年,并赞成长日论。他认为创世记里的家谱没有年代价值,因此认为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时间接近20万年,而非2000年。他说,圣经中的家谱“总之伸缩性很大,可以延展开来以容纳任何合理的时间要求。” [67] 尽管霍奇父子和沃菲尔德有好的意图和真诚的福音派信仰,但他们在圣经真理上的妥协,部分地导致沃菲尔德去世后,自由派神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终胜利。[68] 传道人查尔斯·丹普尔顿(Charles Templeton)悲剧性的灵命灭亡(稍后讨论)就是后果之一。
斯科菲尔德(C.I. Scofield)在他的《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1909)中对创世记1:2的注释中用了间隔论,影响了20世纪全球数百万基督徒。这个注释只是一个断言,没有提供任何依据。针对当时自由派神学席卷教会的挑战,为了捍卫正统基督教教义,12卷《基要教义》(The Fundamentals)于1909年出版。这套书的68篇文章,大多数至今仍值得一读。[69] 但其中有四篇是关于科学的文章,四篇文章都向亿万年的历史观妥协,接受了地质学家的说法,而很少关注创世记经文的细节。
威尔第·史密斯(Wilber Smith)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圣经教授,先后执教于慕迪神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和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45年,史密斯写了一本捍卫基督教信仰的巨著《因此,站着》(Therefore, Stand)。在序言中他警告说,基督徒不应在我们的文化中“妥协于这些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倾向”。[70] 但在他长达86页的有关创造的一章中,他实在妥协于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倾向。因为他完全忽视了挪亚大洪水,接受地质学家倡导的亿万年的地球历史,还提出长日论。他坚持说圣经没有讲地球的年龄,他忽视创世记的家谱,忽视创造的天数,以及“晚上”和“早晨”的多次重复,忽视出埃及记20:8-11中上帝亲自对六日创造的评论 。因为科学证明了物种的稳定性,[71] 也因为亚当和夏娃受造之后,上帝就完成了他的创造工作,所以他才拒绝达尔文进化论。他学识渊博,但他误导读者,说受造之物只有6000年历史的信仰是“中世纪的认定,没有圣经的基础。”[72] 最近,已故的车理深推断说:
“从创世记第一章字面上的意思看,直觉是整个创造过程发生在六个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内。如果这是希伯来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 这似乎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冲突,现代科学说地球是数十亿年前创造的”。[73]
同样,布鲁斯·沃特克(Bruce Waltke)断言道:
“创造的六日,也可能给将经文视为严格的历史记载带来困难。当代科学家几乎一致地否认了一周内创造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否认地球科学的证据。”[74]
前面这些旧约教授们相信,地质证据或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了对创世记第一章进行字面解经是不可接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几十年,基督教学者和领袖们的许多类似声明,显示出他们对创世记的解释,就像过去200年那些前辈的解经一样,受同一件事的牵制或影响。这一件事是:他们认为地质学家已经证明亿万年的历史。结果是,全球大多数基督教大学、神学院和宣教机构,都向亿万年的历史妥协。但是,正如他们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些受尊敬的学者和领袖们显然没有充分地考虑亿万年的神学含义,例如,人堕落前死亡就存在。他们也不理解,其实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均变论和自然主义的)前提假设控制着地质学。[75] 与他们真诚的意图背道而驰,他们接受了实际上严重破坏圣经权威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古老地球论支持者的历史学也需要被纠正。加尔文学院前地质学教授戴维斯·杨(Davis Young)影响着许多神学家接受了亿万年的历史。在谈到19世纪初期古老地球论的拥护者时,他说:
“重读史密斯、希区柯克和米勒(Hugh Miller)令人信服的著作,当代教会将受益匪浅。这些人对创世记的某些具体解释可能会受到批评,但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圣经以外的、与传统的大洪水观念有根本冲突的证据,不是对信仰的威胁,而是更好地理解创世记的机会”。[76]
作为对戴维斯·杨的回答,应该指出,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乔治·杨(George Young)牧师,依据圣经和地质学,驳斥了约翰·派伊·史密斯牧师轻描淡写的释经。乔治·杨牧师通过阅读和野外地质研究,在地质学领域,比史密斯牧师博学多了。[77]
希区柯克和米勒也几乎没有释经。如果他们对上帝话语的解释受到许多批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相信他们对圣经中地质记录的解释?(那些比圣经的命题性真理陈述更难解释),尤其是因为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其他地质学家对地质的解释,而那些地质学家们的前提假设是敌对圣经的。几十年来,戴维斯·杨一直在倡导把世俗的、反圣经的对地质证据的解释当作事实来接受,并用来重新解释经文。此外,史密斯、希区柯克和米勒去世后的几十年表明,这些古老地球理论确实对基督信仰构成了威胁,许多曾经是纯正信仰的教会、神学院和宗派,现在变成了自由派,甚至背叛了信仰。
戴维斯·杨本人正沿着这个滑坡慢慢下滑。1977年,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出版了《创造与大洪水》(Creation and the Flood),这本书对许多神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时他相信,一场平静的全球性大洪水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地质证据,这种不合逻辑的观点实质上把大洪水变成了神话。[78] 到1995年,杨放弃了这一观点,并开始争辩说洪水只局限于中东地区。[79] 而且,多年来,他一直提倡长日论。1990年,他承认他早几年悔改了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基于“对经文的宰割”以及“释经学艺术体操”。但是,所谓的悔改并没有使杨相信创世记是真实的历史,就像教会在前18个世纪所相信的。相反,杨主张完全不合逻辑的观点,他认为创世记第1-11章“也许在以非事实的语言表述历史”。[80]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摆弄经文不能使之符合科学数据”。因此,像大多数地质学家和非地质学家一样,他所标榜的“数据”,其实是对某些数据的解释,而那些解释是基于敌对圣经的前提假设。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应该相信这样思维、这样“悔改”的地质学家吗?即使他自称是福音派。
没有必要的妥协
可悲又可讽的是,过去200年,基督徒为之妥协的创世记第1-11章的真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却越来越被证实,而且常常是由嘲笑及拒绝上帝的进化论者的工作来证实的。莱尔的均变论《原理》一直统治着地质学,直到大约1970年代。当时著名的英国地质学家德里克·阿格(Derek Ager,1923-1993年)和其他进化论地质学家对莱尔的假设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81] 他们认为,许多岩石记录都显示出快速灾难性的侵蚀或沉积的迹象,从而大大减少了许多地质矿床形成所需的时间。阿格这样解释莱尔对地质学的影响:
“我不是历史专家,却花如此篇幅讨论历史,就是一直在试图说明我认为地质学是如何落到理论家们的手里的(阿格在这里指的是均变论者)。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实地观察的影响。就像史蒂芬·古尔德(Steve Gould)所说的那样,查尔斯·莱尔‘成功地说服了后世的地质学家,地质科学是从他始创的’。换句话说,我们允许自己被洗脑,要我们尽力避免用任何极端的和可能被称为‘灾难性’的过程来解释过去。”[82]
现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莱尔式的均变主义洗脑术蒙蔽了世人,使人看不见灾变过程的证据,这当然会使人看不见创世记中描述的长达一年的全球性大洪水的任何证据。同理,新灾变论者阿格既然拒绝了上帝启示的对挪亚洪水的准确无误的历史记载,就继续坚称地质学没有证实大洪水。他看不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正如保罗所说,世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罗1:18-20)。
在重新解释岩石形成的新灾变主义理论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大洪水地质学”理论的复兴。“大洪水地质学”对岩石记录的解释,与19世纪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们的解释非常相似,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洪水地质学”基本上是由魏德孔博士和亨利·莫里斯博士出版《创世记大洪水》(1961)而开启的。如今,这一运动正遍及全球,[83] 其科学模型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84] 基督教学者和领袖们有责任了解不断增长的科学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创世记字面意思的真实性。说创造论者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不从事真正的科研,这是愚昧或误解。本书的附录中推荐一些资料,它们对验证创世记的部分科学证据提供了解释。我要特别推荐莫幼涵(John Morris)的《年轻的地球》(The Young Earth)和唐·德杨(Don DeYoung)的《是数千年,而不是数十亿年》(Thousands, not Billions,书中附带同名的纪录片光盘DVD)。
妥协的灾难性后果
19世纪初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反对古老地球地质学理论,不仅因为古老地球理论反映出错谬的科学推理,与圣经背道而驰,还因为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基督徒对此类理论的妥协,最终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将危害教会的健康,毁坏教会在堕落世界里的见证。英格兰教会神父亨利·科尔(Henry Cole)写道:
“然而,许多尊敬的地质学家通过区分圣经中的历史部分和道德部分来表达对上帝启示的敬畏,并认定圣经中只有道德部分是上帝启示的绝对真理,历史部分并非如此。因此,圣经的历史部分,可以接受任何程度上的哲学和科学的解释,可以被修改或否定!经过这些无礼的离经叛教之人的修改和切割,上帝的话语中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是启示的,因为抽象的道德启示、指示和律例中占圣经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其他三分之二的圣经,可以随意进行科学修改和解释;或者,如果有必要,可以完全拒绝!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人面前宣告不相信上帝所启示的话语的任何一部分,他在神面前根本就不相信它是上帝启示的!……这样的事情在一片拥有上帝启示的土地上必定产生什么后果?时间将在其开篇的几页迅速而可怕地展示国民的怀疑、不忠和背叛,也将看见上帝公义的报应降临在这片土地上!”[85]
科尔和其他反对古老地球论的人明白并警告我们说,圣经的历史部分(包括创世记第1-11章)是圣经的神学和道德教义的基础。破坏了圣经历史的可信度,迟早(可能数十年后),我们会在教会内和教会外看到圣经的神学和道德被抛弃。曾经是基督教国家的欧洲和北美的后续历史发展,证实了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们对教会和社会的最可怕的担忧。
查尔斯·丹普尔顿(1915-2001)就是在圣经的历史部分上妥协而造成恶果的无数悲剧性例子之一。作为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同龄人和朋友,许多人认为他比葛培理更有才华。他曾经在北美和英国向成千上万的人传道,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但是他有进化论方面的问题,于是在1940年代后期去普林斯顿神学院深造以寻求答案。那个时候,这所霍奇父子和沃菲尔德曾经执教的神学院,已经沉醉于自由派神学理论之中。丹普尔顿的教授们说服他必须接受进化论和亿万年的历史,从而破坏了他对作为圣经根基的创世记的信心,毁坏了他对福音的信仰。从神学院毕业后,他又传道数年。但最终,他破碎的信仰迫使他离开全时间事奉,进入新闻界。2001年,他以悲惨的无神论身分去世。1996年,他出版了《告别上帝:我抛弃基督教信仰的理由》(Farewell to God: My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Christian Faith)。他在书的结语中写道:“我不相信具有人类属性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圣经中的上帝不存在。生命只是永恒的进化力量的产物,经过了亿万年的进化,达到现今这种暂时的状态。”[86]
错误的观念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教会,尤其是教会领袖和学者们,现在不能再忽视地球的年龄了!不能忽视日益增多的证实上帝之道的科学证据了! 教会必须为向亿万年妥协而悔改,为无视或不信全球性挪亚大洪水而悔改,再次相信并宣讲创世记第1-11章的字面真理。
[1] 本章取材于过去发表过的书中的两章内容(经出版社授权)。见Terry Mortens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Old-Earth Geological Timescale” in John K. Reed and Michael J Oard, eds., The Geologic Column (Chino Valley, AZ: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Books, 2006), p. 7–30和Terry Mortenson, “Where Did the Idea of ‘Millions of Years’ Come From?” in Ken Ham, ed., The New Answers Book 2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8), p. 63–73.
[2] 他相信乌雪(James Ussher)的说法,认为创造发生于4004 B.C.
[3] 又见Terry Mortenson,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The Church’s Catastrophic Mistake on Geology — Before Darwin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 p. 40–47. 书中讨论了19世纪初之前的解经家的观点,他们大都遵循乌雪主教4004B.C.的创造日期。关于教会历史上东正教的观点,见Terry Mortenson, “Orthodoxy and Genesis: What the Fathers Really Taught” (a review of Fr. Seraphim Rose’s book Genesis, Creation and Early Man [St. Herman of Alaska Brotherhood, 2000]), www.answersingenesis.org/tj/v16/i3/orthodoxy.asp.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views of the commentaries us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4] Charles C. Gillispie, ed.,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New York: Scribner, 1970–1980, 16 vol.), 2:578–579. 此后本章称该书为DSB.
[5] William B.N. Berry, Growth of a Prehistoric Time Scale (San Francisco, CA: W.H. Free- man, 1968), p. 36 and 38.
[6] Gillispie, DSB, “Werner, Abraham Gottlob,” 14:260–261.
[7] 法语原文于1812年面世。
[8] William Smith, A Memoir to the Map and Delineation of the Strata of England and Wales, with part of Scotland (London, 1815); William Smith, Strata Identified by Organized Fossils (London, 1816); William Smith, Stratigraphical System of Organized Fossils (London, 1817).
[9] Michael Foote and Arnold I. Miller, Principles of Paleontology (New York: W.H. Freeman, 2007), p. 150–151; and Charles C. Plummer and David McGeary, Physical Geology (Dubuque, IA: Wm. C. Brown, 1993), p. 167.
[10] Nicolaas A. Rupke, The Great Chain of History: William Buckland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Geology 1814–18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 60–61.
[11] V. Paul Marston, “Science and Meta-science in the World of Adam Sedgwick”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84), p. 528–543. 作者仔细研究了塞奇威克所有的科学方面的作品。
[12] Adam Sedgwick, review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London, 1845), The Edinburgh Review, vol. LXXXII, no. 65 (July 1845). Quotes from pages 3 and 85.
[13] The Declaration of Students of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London, 1865).
[14] William Buckland, On 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as Manifested in the Creation: Geology and Mineralogy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 (London: John Murray, 1836, 2 vol.), I:16 and I:94–95. 这是1830年代发表的、从设计中论证神的存在的八卷“布里奇沃特论”之一。
[15] James A. Secord, Controversy in Victorian Geology: The Cambrian-Silurian Dispu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6), 6.
[16] William Broad and Nicholas Wade, Betrayers of the Truth: Fraud and Deceit in the Halls of Science (London: Century Publishing, 1982). 两位作者都是备受敬重的世俗科学新闻记者。
[17] Colin A. Russell, “The Conflict Metaphor and Its Social Origins,”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1:1 (1989): p. 25.
[18] Martin J.S. Rudwick,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 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431–432.
[19] Charles Lyell, “Review of Scrope’s Memoir on the Geology of Central France,” Quarterly Review, 36:72 (1827): p. 480.
[20]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76.
[21] “Buffon”, DSB, 第2578页.
[22] Comte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London: Strahan & Cadell, 1781, William Smellie, transl., 8 vol.), 1:34.
[23] 被引用于Arthur 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5), p. 43–44. 书中未注明出处。后半部分可见于赫顿的 Theory of the Earth (Edinburgh: William Creech, 1795, 2 vol.), 2:547. 我在赫顿著作的上下卷中都找不到前半部分,在赫顿1788年发表的同名期刊论文中也没找到。
[24] Hutton, Theory of the Earth, 1: 273.
[25] 被引用于J.J. O’Connor and E.F. Roberts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June 2004, www-history.mcs.st-andrews.ac.uk/Biographies/Buffon.html, accessed October 8, 2008.
[26] 被引用于Martin J.S. Rudwick, “Charles Lyell Speaks in the Lecture Theat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9:32 (1976),: p. 150.
[27] 被引用于John Hedley Brooke,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Geologists: Some Theological Strata,” in L.J. Jordanova and Roy S. Porter, eds., Images of the Earth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onograph 1, 1979), p. 45.括弧内的文字是加上去的。弗莱明是长老会牧师、动物学家,倡导古老地球和平静的挪亚洪水。
[28] 被引用于Roy Porter, “Charles Lyell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of Ge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9:2:32 (July 1976): p. 93.
[29] 安德烈·乌雷是著名的化学家,是反对古老地球地质理论的圣经地质学家之一。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讨论,尤其关于他在1829年出版的《地质学新体系》(New System of Geology), 见Mortenson, Great Turning Point, p. 99–113. 书中也讨论了另外六名圣经地质学家的生平和著作。
[30] Katherine M. Lyell,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 Bart. (London: John Murry, 1881), 2 vol.), I:268–271. 括弧里的词语是加上的。
[31] Roy S. Porter, “Charles Lyell and the Principles,” p. 91.
[32] “Buffon,” DSB, 2:577–578.
[33] John H.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p. 238–240.
[34] Ibid., p. 243.
[35] Leroy E. Page, “Diluvialism and Its Critics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C.J. Schneer, ed., Toward a History of Ge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p. 257.
[36] A. Hallam, Great Geological Controvers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
[37] “Werner,” DSB, 14:259–260.
[38] Dennis R. Dean, “James Hutton on Religion and Geology: The Unpublished Preface to his Theory of the Earth (1788),” Annals of Science, 32 (1975): p. 187–193.
[39] 史密斯自己的作品表明了这种模糊的自然神论,地质学家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ips)是史密斯的外甥和弟子,也是这样评论的。见John Phillips,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 (London: John Murray, 1844), p. 25.
[40]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p. 247–248.
[41] Colin A. Russell, Cross-currents: 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Faith. (Leicester, UK: IVPress, 1985), p. 136.
[42] Philip Gingerich, Journal of Geological Education, 31 (1983), p. 144. 金格里奇是研究鲸化石的领袖人物,密执安大学古生物学教授。
[43] C. John Collins, Science and Faith: Friends or Foes? (Wheaton, IL: Crossways, 2003), p. 247.
[44] 我的书记录了这些受过按立的神职地质学家如何不理会圣经,见 Mortenson, Great Turning Point, p. 200–203.
[45] 柯林斯在对这一段的注释中表示他读了达勒姆普尔的一篇24页的关于同位素测年法的文章,并参考了五本世俗地质学教科书。但他似乎只读过奥斯汀的五篇4页长的文章(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同位素测年法)。
[46] Collins, Science and Faith, p. 250.
[47] Mortenson, Great Turning Point (2004)一书详细讨论了七位最杰出的圣经地质学家,他们的论证驳斥了新兴的古老地球理论和其他的向亿万年的观念妥协的基督教思想。
[48] William Hann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Chalmers, D.D., LL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3, 3 vol.), 1:390.
[49] Francis C. Haber, The Age of the World: Moses to Darwi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 202–202
[50] Hanna, Memoirs, 1:193–197.
[51] George Stanley Faber, A Treatise on the Genius and Object of the Patriarchal, Levitical and Christian Dispensations (London, 1823, 2 vol.), 1:111–166. 他在第141页说亚当之前至少有6000年,在156页说创造的日都“相当漫长”。
[52] 同上,第1卷第126页。和今天一样,那时候(1823年)的化石次序与创世记的次序有许多不同点。当时对化石记录的知识正迅速积累,但是法伯所参照的地质著作都过时十年以上了。同上,第1卷第121页。
[53] 同上,第1卷第121页。
[54] 同上,第1卷第115-116页。
[55] John Fleming, “The Geological Deluge, as Interpreted by Baron Cuvier and Professor Buckland, Inconsistent with the Testimony of Moses and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 XIV:28 (April 1826): p. 205–239.
[56] John Pye Smit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oly Scriptures and Geological Science (London: Jackson and Walford, 1839), p. 154–159 and 299–304.
[57] Nigel M. de S. Cameron, Evolu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Exeter, UK: Pater- noster Press, 1983), p. 72–83.
[58] C.H. Spurgeon, “Election” (1855),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Pasadena, TX: Pilgrim Publ. 1990), vol. 1, p. 318.
[59] C.H. Spurgeon, “Hideous Discovery,”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Pasadena, TX: Pilgrim Publ., 1986), Vol. 32 (Sermon 1911, given on 2July 25, 1886), p. 403.
[60] Charles Spurgeon, Jesus Rose for You (New Kensington, PA: Whitaker House, 1998), p. 45–47. 出自他12月17日的讲道“基督,死亡的毁灭者”( Christ, the Destroyer of Death)” 。他对地质学的评论在第一点“死亡是敌”中。
[61]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7, 3 vol., reprint of 1872–73 original), 1:570–71 and 2:40–41.霍奇在第一卷关于创世的一章中只引用了创1:2, 1:3, 1:14, 1:27, 2:4, 和 2:7,但从未解释经文。他在第二卷关于人的起源一章中仅在第一段中引用了创1:26-27和2:7。关于人类的历史,他相信创5和创11中的家谱中错过了人名,所以并不是按时间顺序。他跟随的是他在普林斯顿的旧约学同事William Henry Green的说法。
[62] 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Outlines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1, reprint of 1879 revised edition), p. 245–246.
[63] Morton H. Smith, “The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Doctrine in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es,” in Joseph A. Pipa Jr. and David W. Hall, eds.,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Whitehall, WV: Tolle Lege Press, 2005), p. 7–16.
[64] Mark A. Noll and David N. Livingstone, Evolution, Science and Scripture: B.B. Warfield, Selected Writings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0).
[65] 同上,第213页。
[66] 例如,J. I. Packer就是这么认为的。同上,第38页。
[67] 同上,第222页。
[68] 关于这三人在长老会里针对进化论的辩论中的影响,见Smith,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Doctrine,” p. 7–16. 在美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过程中,古老地球进化论起了突出的作用。有关这方面的启发性讨论,见 Jon H. Roberts and James Turner,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69] 见R.A. Torrey, ed., The Fundamentals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90, reprint of 1958 edition).
[70] Wilbur M. Smith, Therefore, Stan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45), p. xiii.
[71] 同上,第325-327页。可悲的是,他只是引用了著名科学家的话语,而只字未提创世记清晰地教导神创造了截然不同的动植物,让它们各从其类繁殖。
[72] 同上,第312页。
[73] Gleason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Chicago, IL: Moody Press, 1985), p. 18.
[74] Bruce K. Waltke, Genesi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1), p. 77.
[75] 作为例子,我分析了三位著名神学家的古老地球论证:“Systematic Theology Text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A Response to the Views of Er- ickson, Grudem, and Lewis & Demarest,” Answers Research Journal 2 (2009):175–199, www.answersingenesis.org/articles/arj/v2/n1/systematic-theology-age-of-earth.
[76] Davis Young, The Biblical Flo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152.
[77] 见Mortenson, Great Turning Point, p. 157–178关于乔治·杨的一章。
[78] 为期一年的全球性大洪水,其用意不仅是消灭一切陆生动物、人类和鸟类,而且要摧毁地球的表面(创6:7,13),涉及到全球性的暴雨(24小时不停,至少40天,也许150天)和地壳板块运动(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150天。短短的4500年怎能抹去如此一场洪水的痕迹?这不合逻辑。但杨氏相信 (Creation and the Flood,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7, p. 172–174)地域上和时间上更为有限的小洪水或者逐渐的地质变化过程却留下了数千英尺厚的地层学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承受了亿万年的时间,甚至经历了大洪水,而面目依然!这又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信条。
[79] Davis A. Young, The Biblical Flo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242.
[80] 杨是如此解释他的结论并描述他的“悔改”的:“长日假说坚持认为,经文里至少显示创世的日子是长而不确定的时期的可能性,但是紧邻的上下文提示,翻译成‘日’的‘yôm’ 一词指的确实是‘日’……长日说练就了跨越文字障碍的非凡的本事。”杨氏在讨论了创世记第1章和进化论历史在事件顺序上冲突的几个例子以后,继续说:“然而,这些明显的冲突之处并没有阻止动机良好的基督徒,包括之前的我自己,曲解经文,使之表达它本没有说的意思。我曾提议每天的事件有重合。几年前我公开地悔改了对经文的宰割,重新开始,以免让自己更难堪。”
杨氏又审视了协调创世记与古老地球地质学的其他的失败的技巧,然后坦白说:“这些技法可能都是天才的,但一眼就能看出其勉为其难的本质。虽然这些释经学艺术体操展示了惊人的灵活性,我猜想这些做法都造成了神学肌肉的临时性损伤。把创世记第1-11章解释成历史事实与科学研究所揭示的早期宇宙史和人类历史图像不契合。摆弄经文不能使之符合科学数据。”他的结论是:“圣经也许在以非事实的语言表述历史。”Davis Young, “The Harmonization of Scripture and Science” (1990 Wheaton symposium), quoted in Marvin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2), p. 232–234. 我存有这次讲座的完整录音带。
[81] 除了阿格的著述以外,近年揭露均变论谬误的其他作品(都是非创造论者)包括Edgar B. Heylmun, “Should We Teach Uniformitarian- ism?” Journal of Geological Education, vol. 19 (Jan. 1971):p. 35–37; Stephen J. Gould “Catastrophes and Steady State Earth,” Natural History, vol. 84, no. 2 (Feb. 1975): p. 14–18; Stephen J. Gould, “The Great Scablands Debate,” Natural History (Aug./Sept. 1978): p. 12–18; James H. Shea, “Twelve Fallacies of Uniformitarianism,” Geology, vol. 10 (Sept. 1982): p. 455–460; Erle Kauffman, “The Uniformitarian Albatross,” Palaios, vol. 2, no. 6 (1987): p. 531.
[82] Derek Ager, The Nature of the Stratigraphical Record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46–47. 阿格的最后一本书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叫做《新灾变论》(The New Catatroph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书中记录了他在全世界观察到的沉积层被灾难性地沉积和侵蚀的地质学证据。他在《新灾变论》中说,“我也许应该就本书的书名说几句。正像政治家会重写人类历史一样,地质学家也会重写地球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地质界一直被查尔斯·莱尔的渐进均变论所主导,或者说被洗脑。任何提示‘灾难性’事件的说法都被认为是过时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可笑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居维叶学派某些人的极端做法,虽然居维叶本人并非如此。另一方面还有显然站不住脚的以圣经为中心的极端主义观点,痴迷于挪亚洪水之类的神话及复仇女神式的古典主义思想。我想有必要做以下声明:鉴于以往我的话语遭受的误用,我希望,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可以被断章取义,无论如何不可以认为支持‘创造论者’的(我拒绝称之为科学)观点(第xi页)。
[83] 即使进化论者也注意到创造论组织已经遍及30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韩国的组织包括2000多位科学家。见 See Debora MacKensie, “Unnatural Selection,” New Scientist, no. 2235 (April 22, 2000): p. 38.
[84] 由年轻地球创造论的硕士和博士根据文献或实地考察而撰写的经同行审议的地质学论文经常性地发表于《创造研究协会季刊》(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创造杂志》(Journal of Creation),和网上的《解答研究杂志》(Answers Research Journal),及自1986年以来每4年在匹兹堡召开的国际创造论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上。
[85] Henry Cole, Popular Geology Subversive of Divine Revelation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34), p. ix–x, 44–45 (footnote).
[86] Charles Templeton, Farewell to God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6), p. 232. 他的悲剧性故事见于Ken Ham and Stacia Byers, “The Slippery Slide to Unbelief,” Creation ex nihilo 22:3 (June 2000), p. 8–13, www.answersingenesis. org/creation/v22/i3/unbelief.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