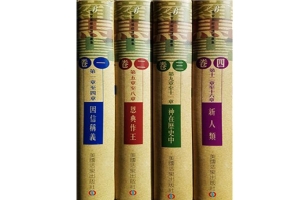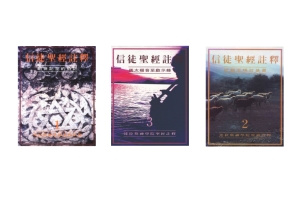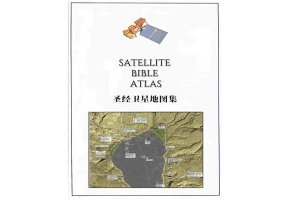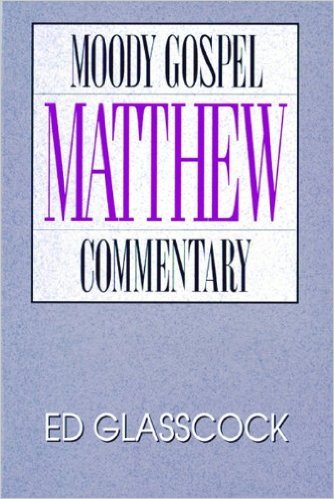第一章:教会先贤对创造、洪水和地球年龄的见解
詹姆斯·穆克(James R. Mook)[1]
有关魏德孔博士的个人手记
我在读圣经学院和初次在教会青年部服事的时候,读过魏德孔博士与亨利·莫里斯博士合著的《创世记大洪水》(The Genesis Flood)。那是我初次接触魏德孔博士的著述。我是在公立学校接受的教育,只学过进化论,从未听说过创造科学。
20世纪70年代,当我参与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时,我希望高中生们阅读和学习创造科学,以使他们认识到创造科学的合理性,并使他们能够机智应对高中乃至以后大学里提倡进化论的理科教师。那些高中生们发现魏德孔博士的著作极具启发性。到了90年代,当我在神学院做教授教书期间,我的学生们也发现魏德孔的著述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效。他们由此注意到了达尔文主义不科学的哲学前提,并发现地质学数据与圣经所记载的创造和大洪水在科学上相吻合。
近些年我终于见到了魏德孔博士。我发现他是一位敬虔、友好、善良而又严谨的神学家和护教士,也得以亲自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赞赏。我要在此重申,感谢他勤奋而勇敢的工作,感谢他在教会内外直面并驳斥有关起源的进化论地球历史概念。
教会先贤的立场对地球年龄争议的重要性
创世记最初的几章是整部圣经的根基。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如果推翻了这些章节,其余的经文也确实没有什么持久的意义了。基督教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基于这几章。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作者们如此注重这些章节的原因之一。这也提醒了我们,神学发展的历史本质上是释经学的历史。
自教会成立以来,先贤的释经学一直在神学辩论和阐明正统的标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于基督论、三位一体论和经典化的争论很激烈,有时数百年难解。早期教会内曾有像亚他那修(Athanasius)那样的信徒,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 (犹大书1:3),如今有哪位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不会为之感恩戴德呢?
直到如今,有关地球年龄的争议仍在继续。人们再度关注教会先贤,看他们是如何解释创造日子的长短、地球年龄和创世记大洪水之类的问题的。[2] 由于人们一直想探寻他们在神学问题上的观点,可以预料,当人们在谨慎地使用他们的智慧的同时,难免会有人倾向于曲解先贤们的著作。正如对待圣经一样,对待先贤的教义也同样会有断章取义、搀入己见或者遮盖本意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知名作者募集了教会先贤来接受深度时间的观念。威廉·谢德(William G.T. Shedd)等学者们认为自先贤时代就有人教导长日创造论。亨利·布洛克(Henri Blocher)声称奥古斯丁持有类似框架理论的观点。阚亚瑟(Arthur Custance)把俄利根(Origen)当作间隔论的拥护者。这些五花八门的见解给普通读者带来极大的困惑,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这些现代学者们具体地使用了哪些古典论著来将古人划归于后达尔文式的类别呢?其次,这些现代作者有没有遗漏什么著述资料?第三,如果有资料被忽视,是否由于只参考了二手材料而造成无意的疏漏?第四,如果我们提出足够的先贤方面的反证,这些作者们在以后的著作中会不会引述这些反证?本章旨在应对一些对先贤的误读,通过分析原始资料来澄清先贤的著作是否真正支持现代深度时间理论。
当代对教会先贤的错解
长日创造论和框架理论的倡导者声称,六日创造主义是较为近期的复古运动,是对均变说和原始达尔文主义的反应。他们提出,早期杰出的释经学者主要追求神学上的意义,而非历史意义,因此不会认同现代年轻地球理论。他们中间有些人质疑先贤的观点与当前的辩论是否有关,但另一些人,如休·罗斯(Hugh Ross),则很清楚地说,教会先贤的认可对于一种神学立场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像谢德、波洛克和阚亚瑟等人一样,休·罗斯试图用先贤的力量来支撑他的年老地球立场。他们所有的提议都似乎包含四条共同的逻辑:首先,这些现代年老地球论者都认为,在早期教会澄清和强化其信条的过程中,地球的年龄对基督教的基要真理并没有那么重要。第二,这意味着(甚至昭示着),如果这些敬畏上帝的先贤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关于宇宙年龄的各种各样的释经法和释经学结论,我们也应当效法他们。第三,他们宣称先贤的著述足以证实,年轻地球创造论并非早期教会的立场,也绝对不是正统教会所必须坚持的传统。第四,每当现代学者引用奥古斯丁等先贤,称他们认可深度时间的时候,关键的前提似乎是,相信亿万年并非是向均变论让步,反而是符合历来正统的立场。
基督徒应当意识到教会历史上有大量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明智地使用先贤的观点是有意义的,有启发性的。[3] 虽然基督徒的最高和最终权威始终应该是经文,但是人们对教会历史的了解越多越好。有了先贤的指引,我们会有更好的装备来辨别和应对古往今来层出不穷的神学异端。
休·罗斯对先贤的运用可以在《创造与时间》(Creation and Time)和后来与车理深合著的《创世记争论》(The Genesis Debate)中找到。[4] 但是他向先贤最强的诉求见于《几天的事》(A Matter of Days)一书中。这本书中“时代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 一章专门阐释了早期教会先贤对创造日的长度相对不太关注。休·罗斯指出,凡提到该话题的都不把一个创造日当作24小时。他进一步断言,现存的著作表明,先贤“承认”创造日子的长短“对他们的理解和解释而言是一种挑战”。因此,除了奥古斯丁之外,他们“只是暂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仁慈地包容多种观点”,而不是教条地只坚持一种解释。[5]
再早,休·罗斯辩称:“许多早期教会先贤和其他圣经学者把创世记第1章的创造日解释为长久的时间段。”他认为爱任纽(Irenaeus)、俄利根、巴西流(Basil)、奥古斯丁和阿奎那(Aquinas)都是长日创造论的倡导者。[6] 尽管休·罗斯在这里比先前在《创造与时间》的“早期教会领袖的解释”(“Interpretations of Early Church Leaders”)[7]一章里稍加谨慎了些,但他的描绘仍然基本相同,因此仍然很不准确,如下文所示。对教会先贤的自然解读表明,虽然他们对创造日有不同的观点,而且都(正确地)注重创造的神学意义,但是他们都明确地肯定地球是在距他们不到6000年之前瞬间被造的。他们没有给休·罗斯等现代人提倡的“年老地球”留下余地。
教会先贤的自然主义时代氛围
按常识来说,我们同意休·罗斯的观点,即教会先贤不可能受过达尔文主义或现代地质学上的年老地球论的影响。[8] 这看似不言而喻的事实却忽略了一点,即在基督时代之前,各种进化和均变论概念已经融入了希腊思想。[9] 早期的护教士坚持圣经关于创造的启示,反对希腊的宇宙学。例如,罗马的一位长老,希坡律陀(Hippolytus,约公元170-225或235年)非常熟悉希腊的许多自然主义教导,并一一摒弃。在《所有异端的驳斥》(The 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第一部中,他对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各种观点加以定义并总结道:
“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宇宙是从没有质量的统一体而产生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没有质量而在各个方面都容易发生变化的物体,构成了宇宙的起源原理。因为当这种变化发生时,就会产生火、风、水、地。然而,希帕索斯(Hippasu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米利都人泰勒斯(Thales the Milesian)的弟子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由一个具有质量的实体而产生的。麦塔庞顿人希帕索斯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the Ephesian)宣称火是万物的起源,但阿那克西曼德说是风,泰勒斯说是水,色诺芬尼(Xenophanes)说是地。根据色诺芬尼的说法,‘万物从地而出,且万物回归于地。’”[10]
凯撒利亚主教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公元329-379)时不时提及哲学家们以及他们的宇宙学观点。他反对希腊人的谬误,因为他看到这些学说被后来的新学说一一推翻,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学说持守一个有智能的元初动因,而是将一切归于“偶然”。他写道: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对这个念头赞叹不已……希腊哲学家们上下求索以解释大自然,然而他们的体系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而是被后人一一推翻了。反驳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的理论足以互相推翻。那些愚昧无以认识上帝的人不能容许或接受宇宙诞生于智者的设计。这是导致他们陷入可悲后果的主要谬误。他们中有的求助于物质原理,将宇宙的起源归因于世界里的元素;另一些则幻想原子、不可分割的物体、分子和通道通过它们的结合而形成可见的自然世界。原子的重聚或分离产生了生与死,而最持久之物的构成仅仅是由于其原子间相互粘合的强度高:这些作者赋予天、地、海如此不堪一击的起源,且鲜有一致性,他们编织的理论如蛛网般脆弱!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们内心的无神论误导了他们,在他们看来宇宙似乎没有治理和统领,一切都是出于偶然。为了防止这种错误,创世记从一开始就用‘上帝’二字来启发我们的理解:‘起初,上帝创造。’”[11]
另外应当考虑拉克唐修(Lactantius,约公元250-325)的著述。他强烈反对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年老地球论:
“因为对万物的起源和世界的创造的那个原始时期的无知,柏拉图等诸多哲学家宣称说,这个美丽的世界在数千个时代之前已经形成了。他们也许在此沿用了迦勒底人的观点。正如西塞罗(Cicero)在他的第一本关于占卜的书中提到的那样,迦勒底人愚蠢地讲到自己的纪念物已经存在了47万年。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不可能为此而被定罪,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散布谬误。但是,我们这受过圣经教导认识真理的人知道世界的起源和终结。在第二卷已经谈到了起源,所以在本卷结束的时候要谈到终结。那些认为从世界起源之后已经过去数千个时代的哲学家们需要知道,第六千个年头至今尚未完结。等六千年的数目满足之后,大结局即将来到,人类事务的状况将被重塑改善。这里需要先呈现证据,为让这事件本身显而易见。正如充满奥秘的圣经上所记载的,上帝在六天的时间内完成了创世之工,他所造的自然界令人惊羡,第七日歇工,并将第七日分别为圣。这就是安息日,在希伯来文就是第七日,因而数字七代表合理完整。因为有七天,七天的交替组成岁月的周转……”[12]
所以不能说先贤的创造观念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即没有现代进化论和均变主义观念的压力)。先贤们强调自己的观点主要是为了驳斥与现代思想非常相似的希腊哲学的自然主义起源理论。[13]
创造日的长短
先贤们都赞同瞬间创造,而非渐进。其中按字面解读圣经的人都指明创造的六日各有24小时。寓意解经派,如革利免(Clement)[14]、俄利根和奥古斯丁,并不将创造的日子视为24小时
的一天,但他们也都不认为非字面的日子与年轻地球论有抵触,这一点即使年老地球论的倡导者戴维斯·杨(Davis Young)也不否认。[15]
字面理解的拥护者
在早期教会里,寓意解经派和字面解经派的关系有些紧张。字面解经派的一位著名代表、做过君士坦丁儿子家庭教师的修辞学家拉克唐修,把一个创造日视为24小时。[16] 他引用圣经对创造的记录来反对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年老地球论观点,认为五千多年前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他认为“七日”组成一周,并且“七天的交替组成岁月的周转”。[17] 显然,对拉克唐修来说,创造日与组成一年的每一周的日子相同。
普图伊主教维多利诺斯(Victorinus, 公元304年卒)明确地指出了创造的第一天分为12小时白昼和12小时黑夜。他说:“创造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正如摩西在其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上帝在六天之内为了他威严的装饰而创造这一切的一切,并赐福第七日……最初,上帝创造了光,并将一昼夜各自精确地分为十二小时……那么,如上所述,一天均分为两部分——白天与晚上各十二小时。”[18]
叙利亚的耶福列木(Ephrem the Syrian,约公元306-373年)是一位执事、赞美诗作者、颇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和释经学家,也是少数懂希伯来文的先贤之一。他完全按字面解释创世记第1章里一日的长短:“尽管光和云是在眨眼间创造的,但是第一天的白天和晚上各在12小时内完成。”[19] 耶福列木反对关于创世记一章的寓意解释:
“因此,不要以为神在六日之内的工作是寓意性的。不要说关于这六日的事物是象征性的,也不能说这些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名词或者这些名词象征着其他事物。相反,我们要据此知道最初天与地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创造的。‘天’与‘地’这两个名词并不指代任何其他事物。这里指的就是天与地。神随后的其他工作和被创造的事物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符号,因为它们的名称与其实质内涵相对应。”[20]
凯撒利亚的巴西流著有六日谈(Hexaemeron),是他在四旬斋期间关于创造日的讲道集,[21] 他特别反对“失真的寓意解经”,指责寓意解经派只是“为自己的目的”,“在经文之上自我发明并引以为荣”。相反,他提倡谦虚地接受“常识”,即经文“白纸黑字的字面意义”。[22] 巴西流明确地指出世界的创造是在24小时的日子里迅速完成的。谈到第一天光的创造,他说:“这样,在一瞬之间,通过一句话,万物的创造者就将光赐给了世界。”[23] 注意巴西流对日子的长短讲得很清楚:
“‘有晚上,有早晨,是一日。’(译者注:圣经原文中‘一’用的是基数词,此后几日都用序数词)。为什么圣经说头一日是‘一日’呢?在讲到第二、第三和第四日之前,是否应当把这一系列之首称为‘第一日’呢?既然说是‘一日’,那么其用意就是要确立一昼夜的长短,把黑夜白天的时间段合并为一个概念。一天的时间为二十四小时,就是要把白天与黑夜加起来算。哪怕在夏至和冬至,两个时间段不一样长,但圣经标出的时间依然规范了一定的长度。这好比说:二十四小时为一天的时间段;或说,实际上一天是天空回归到同一个位置所需的时间。日落日出,使晚上或早晨呈现在世界上,其交替的周期总不会超出一天的时间……上帝造出了时间的本质,测定了时间段,用日子作为划分时间的尺度。为了用星期作为另一个时间长度,他让星期自我轮回以计算时间的进程,并规定一日轮转七次为一个星期:周而复始。”[24]
“圣大巴西流”是四世纪最重要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之一,坚决捍卫尼西亚三位一体论,反对亚流(Arius)教派和撒伯流(Sabellius)主义的异端。[25] 他还因救济饥荒而闻名,曾建立贫民院、医院和临终关怀院,并撰写修道院规则。巴西流的六日谈历来被看作最具有实质的六日谈著作,并激发了许多人撰写与六日相关的评论。尼撒的格力高利(Gregory of Nyssa,335-约395年)在他自己的六日谈中说:“圣巴西流关于创世的论述……是唯一仅次于圣经的著作。”他称自己的著作不会“随从大众的观念。”他只不过想“明白……按一定秩序描述创造过程的经文的根本意思,即‘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世记 1:1],以及六天内所包含的其余的关于宇宙创造的经文。” [26]
寓意解经派
教会先贤中的寓意解经派虽然不认为创造日是24小时的真实日子,而仅仅是创造顺序的象征,但他们在抵制当时的年老地球论方面也表现出色。
亚历山大教理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城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约公元150-211或216年)声称六个创造日并非字面意义,而是象征着在时间开始之前一瞬间的创造顺序:
“上帝的安息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代表上帝停止做工。因为上帝本为良善,如果他停止行善,那么他就不再是上帝,而这样说就是亵渎。因此,上帝的‘安息’意味着命定受造物的秩序不被干扰、所有创造物脱离最初的混乱。各日的创造顺序非常重要,使万物按照创造的先后得到不同的尊荣。虽然万物在神的思想里是一同被造的,但各有其不同的价值。既然万物是一起被造的,那么每一样的创造也不是以话音为标志的。毕竟各物必先命名,后创造。万物是出于同一个权能,同时从一本而生,后宣告之物又源于先宣告之物。因为神只有一个身份,一个旨意。既然我们看到时间与存在之物一起诞生,创造何以在时间之内发生呢?”[27]
这一观点,即上帝“同时”并“一起”创造万物,为后来的俄利根和希波的奥古斯丁所拥护。
俄利根(约公元185-254年)也曾为亚历山大教理学院的负责人。尽管如今人们认为他的教导有重大问题,但他还是早期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幸的是,虽然他属于当年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他的大部分著作失传了。他像保罗和奥古斯丁一样饱受争议,被称为 “圣经批判学之父”。他的《论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是东方系统神学的第一部作品。然而,他的主要影响是作为早期教会勾画寓意解经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因而,他认为创造周的六天只是“看起来像”字面上的日。[28] 事实上,俄利根认为有 “理智” 的人不会把创世记第1章解释为“纯粹的事件史”。他声称这些事不要当作真正发生过,而是要理解成属灵意义。[29]另外,俄利根坚持认为创世记第1章的第七天持续到世界的末了。[30]
在同一个段落里,俄利根断言说:“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在福音书中注意到无数类似的经文,因而将确信,在按字面意思记录的历史中,会插入未曾发生过的事件。”[31] 因为福音派人士不能在坚持圣经无误的同时又拥护俄利根对创世记和福音书的概念,那么敏感的读者会要求说明。如果要责备休·罗斯挑选那些支持深度时间的教会先贤,那么创造论者何以不因为引用俄利根而受到类似的责备呢? 我们如何能够认同俄利根关于创世记第1章的某些说法,却不接受其余的,尤其他稍后认为福音不是字面上的历史事件的观点呢?这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对此我们提供七点值得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们在这里搬出俄利根来回应深度时间的倡导者,旨在说明他们为了反对字面意义上的日子而引用俄利根是无济于事的。其次,创造论者很少提及俄利根,除非是强调他偶尔的“年轻地球”类论点,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其历史价值,而不是用他的理念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第三,虽然俄利根的寓意化观点可能在灵修、历史研究或其他方面有价值,但是我们要警戒,对他的论点应该负责任地、谨慎地应用。第四,有些重要因素需要牢记:虽然俄利根没有将创世记第1章看为字面的历史,但他还是肯定了休·罗斯和莱森(Letham)莫名地忽略了的一些内容。例如,在斥责克理索(Celsus)时,俄利根明确地指出“摩西对创世的记载……教导说世界历史远远不到一万年。”[32] 此外,他还专为反对希腊人和埃及人关于“世界没有被创造”而是永久存在的说法而强调自己的这个观点。[33] 莱森和休·罗斯拿俄利根作为对创世记第1章非字面理解的早期前例,但因俄利根(莱森所承认的)新柏拉图式的寓意主义和(莱森没有提到的)对年轻地球的认可,俄利根的话对他们的帮助并不大。[34] 第五,纵然俄利根不从字面上理解创造日,但若称他支持“长日论”或“框架假说”,就是对他莫大的误解。俄利根没有在任何地方阐明这样的论点。第六,在如今的福音派神学院里,俄利根理解经文的方式通常是被当作主要的反面教材来介绍的。如此可疑的解经方法引出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俄利根的许多信念是如此明显地不正统,即使现代的包容主义者也不愿与之为伍。他可能带给人的益处完全被他在释经学上的缺点所掩盖。莱森和休·罗斯说创造论者不承认也不尊重俄利根的权威,这种宣称是误导读者。鉴于俄利根在许多领域不合正统,更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针对莱森和休·罗斯。即,他们为何使用俄利根来帮助支持自己对深度时间的辩解。
奥古斯丁属灵和释经学上的导师、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 约公元338-397年)凭着他对希腊语的了解研究了斐洛(Philo)、俄利根和亚他那修,并与巴西流进行了交流。虽然安波罗修总体上属于新柏拉图学派,是亚历山大式的寓意主义者,[35] 但从他对巴西流六日谈的评论中看出他对六日时间长度的字面理解:
“圣经规定,只有包含白日和黑夜的24小时才称为‘日’,就等于说一日的长度为24小时……在这种算法中,黑夜被看作日的一部分来计算。因此,每当时间轮回一次,里面只有一日。上帝创造了晚上和早晨,圣经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白日和一个黑夜的时间,此后就不再称之为白日和黑夜,取而代之的是用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做为名字: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习惯。”[36]
看来,安波罗修认为创世时的每一个“日”的长度为24小时,而因为白日是24小时内比较重要的那部分,所以“日”这个词也包括了黑夜。
据称,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公元 354-430年)允许创造日长于24小时,因而成为了最常被引用的权威。杰克·路易斯(Jack Lewis)说,奥古斯丁认为创世记第1章是关于未来的寓言。[37] 但他进一步说,奥古斯丁同时想阐明圣经的作者 “关于上帝与世界”究竟想说什么。[38] 奥古斯丁认为创世记2:4提示万物不是六天创造的,而是同时创造的。[39] 根据他的观点,物质和灵魂按其本性被创造,而其余的万物被造时则是隐形的(基本原理)。随着创造之后上帝持续的照应和工作,万物才得以从“基本原理或隐形中”中发展出来。最初的创造没有“任何时间间隔” 。[40] 路易斯指出,这种随天意渐进发展的概念被后来的进化理论系统引以为例。然而以此为例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很显然奥古斯丁相信不同种类的动植物是在一瞬间创造成的。在路易斯看来,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自上帝完成了“第六日” 所描述的创造之后,并没有再创造新的生物。[41]
但是萨尔法提(Sarfati)敏锐地观察到,奥古斯丁因为不懂希伯来文,几乎完全依靠拉丁文圣经。他只是在晚年,在创世记评论完成后很久,才有了对希腊语的基本认识。正如萨尔法提所指出的,因为他不了解希伯来语,也许就不知道希伯来语“即刻”(עַגֶר,参考出埃及记33:5、民数记16:21, 45、以斯拉记9:8)这个词。也许,如果奥古斯丁懂得希伯来语,他就不会拥护万物瞬间创造的看法。但是正如萨尔法提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如此,奥古斯丁的解释“也与年老地球拥护者的主张截然相反!”[42]
奥古斯丁断言,创造的六日难以构想,但那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六天,因为创造的日子只是一天。[43] 路易斯准确地观察到,奥古斯丁认为创世记第1章的六日是给天使和那些无法理解他在一刹那创造一切的人的渐进启示。创世记第1章的日子体现出创世一刹那中的次序,然而,其所描述的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这些日子不是太阳日,也不是漫长时代,而是启示创造在一瞬间之内的进展的标点。[44]
路易斯正确地指出,奥古斯丁不相信创造是在六个字面的日子里完成的。乍看这似乎是与近期创造的观点相悖,但细察并非如此。首先,非字面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年老地球的解释。其次,没有证据表明奥古斯丁(或任何的先贤)支持创造发生在亿万年前的提法。第三,相反,很显然奥古斯丁认为创造是在瞬间发生的。第四,奥古斯丁明确指出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与世界有“万年以上”历史的观点相矛盾。他相信按圣经教导,地球年龄还不到6000年。[45]
“它们也被那些声称世界有万年以上历史的欺骗性文件所迷惑。按照圣经来估算,世界历史不到6000年。”[46]
“总是有人问人类为什么不是在向过去无限延申的若干年代之前被造,而是出现得如此之晚。我告诉你们,根据圣经,从人的诞生到现在还不到6000年……”[47]
切记奥古斯丁相信上帝在一瞬间创造了一切(至少包括万物的基本原理),以免有人以奥古斯丁的观点为依据,说亚当在不到六千年前被造,但其余万物的创造则早得多。另外请注意奥古斯丁的评论,他说那些古老地球倡导者是反对圣经中所阐明的历史的(见下文)。此外,正如下文将要表述的,奥古斯丁认为,创造的“六天”预表了全部的地球历史将持续6000年。
总而言之,我们请那些引用奥古斯丁的权威来捍卫深度时间并反对一日为字面上的24小时的人注意以下六点:首先,他的《创世记解说》(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是基于耶柔米(Jerome)的拉丁文翻译,而不是基于希伯来原文。其次,由于他不了解希伯来语,所以不得不依靠拉丁文。他从未亲自研读过创世记原文。第三,他属于亚历山大学派,该学派以大量使用寓意解经著名,而不是使用严谨系统的语言学方法来解经。第四,他不相信堕落之前有人死亡。第五,他相信字面上的全球性洪水。第六,通过对其著作的现代解读,我们没有把握认为奥氏曾摆脱过他早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鉴于这些事实,年老地球论的倡导者援引奥古斯丁关于创造日长短的观点来支持亿万年历史并反对年轻地球观,是说不通的。[48]
六日的末世预表
通过考查先贤对创造日长度的看法可以得出结论:教会先贤都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支持者,这与休·罗斯等人的说法相反。首先,大多数先贤将一日视为24小时,有些甚至指明了小时的数目。其次,即便有的先贤坚持认为创世记第1章里‘日’的概念只是象征性的,但他们仍然相信创造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甚至是在一瞬间——完成的。第三,先贤的著作中并没有任何章节可以供现今的年老地球创造论者用来支持创造日为亿万年漫长时代的说法。
教会先贤中有一种六/七千年时代论,认为地球年龄少于6000年并在6000年后不再保持当前状态。这一观点更进一步证明他们支持年轻地球创造论。在教会历史的前两个世纪,教会先贤相信前千禧年末世论,认为第七个千年就是千禧年。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而且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无千禧年论变成了主流的末世论。但即使在末世论转变之后,先贤们仍然保留着6000年的世界历史框架。
背景
六/七千年时代论是出自对六个创造日的类比解释。根据诗篇90:4 和彼得后书3:8(“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先贤们认为创造周的每一天代表未来地球历史的一千年。[49] 这种类比预表学说(类型学)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已经存在。19世纪的泰勒(D.T. Taylor)总结了许多有关六/七千年时代概念的文献。[50] 他指出,根据18世纪的天文学家大卫·格里高利(David Gregory)的说法,古代的卡巴拉学派[51]最早提出六千年历史的概念,其根据有两点:1. 在创世记1:1中,希伯来字母aleph出现了六次,而aleph在犹太算术中是代表1000的符号;2.创造周为六日,而且一日如千年。泰勒指出,普鲁塔克(Plutarch)说迦勒底人、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er)和波斯人认为人类历史将持续6000年。阿诺德·埃勒特(Arnold Ehlert)也指出,陀斯卡拿人(Tuscans)、波斯人和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认为创造过程包含了六个千年时代,而此后人类又将存在6000年。[52] 当时的犹太拉比对于从六日类比中发展出的末世论尤其坚持。埃德斯海姆(Edersheim)在对《塔木德》(犹太公会版本)的总结中提到了卡蒂娜(Kattina)拉比基于诗篇90:4的见解:
“世界将持续6000年,根据以赛亚书2:17的预言,其中有一千年的荒凉时期。澳巴伊(R. Abayi)根据何西阿书6:2,认为此状态将持续两千年。然而,这些经文也用来支持卡蒂娜的见解,他认为每逢一个七就有一个安息年,这里的一天等于一千年的荒凉与安息——经文根据是以赛亚2:17、诗篇92:1和诗篇90:4。”[53]
尼西亚会议之前的前千禧年论者
殉教者贾斯汀(Justin Martyr, 公元100-165年)向犹太人特里弗(Trypho)宣称,“有主见的基督徒”相信,从死里复活之后,将有“在耶路撒冷的一千年。到那时,这座城市将被重建、装饰和扩建,正如以西结和以赛亚等先知所宣示的那样。”[54] 贾斯汀认为,亚当未满1000年而死——如同神所警告的那样,他死在了吃树的果子的 “那一天”。由此可以看出贾斯汀 “一天” 预表一千年的概念。他把一天的预表性与“‘主看一日如千年’的话语”连在一起。然后,他将这种说法和使徒约翰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凡信我们的基督的将在耶路撒冷居住一千年,此后将发生普遍性的、永恒的复活,全人类受审判。” [55]
《巴拿巴书》(公元130-131年)里有接受这种六日类型学的早期迹象。以十诫中关于安息日的诫命为基础,该书信说六日是指上帝在当今世界的做工将在6000年后结束。而在“第七日”之初,基督将第二次降临并开启他的安息日。耶稣复活的“第八日”将成为新天新地里复活的众圣徒最后的安息日。[56]
克鲁奇菲尔德 (Crutchfield) 指出,巴拿巴认为第一到第五天预示历史的前5000年(过去)。他认为第六天是指他自己的时代,即第六个千年时代(当今)。第7天是对千禧年的预言,乃是第七个千年时代,而第8天所预言的是永恒的状态。后来的许多先贤,甚至于那些不认同巴拿巴的前千禧年论的(例如俄利根和奥古斯丁),都响应他这种类型学的使用。他们将第七天视为永恒的状态。[57]
里昂主教爱任纽(公元130-202或212年)是早期教会里第一位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他坚决反对诺斯底主义,认为《启示录》中的数字666概括了这种 “六千年中发生的最大的叛教事件”。他随后申明,世界将在与创造世界的天数相应的千位数“终结”。创世的六天与上帝安息的第七天是“对先前所造的事物的说明,也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言。”将创造日与末世论关联在一起的基础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在六天之内万物创造完毕,由此可见,万物将在第6000年终结。”[58] 爱任纽接着描绘了前千禧年论者对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场景。当“敌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统治“三年零六个月”之后,主将再临,将敌基督和他的追随者“送入火湖”,并开启“国度的时代……带来安息……,即神圣的第七天。他将恢复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即主所宣称的‘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国度。”[59]
希坡律陀在评论但以理书第2章的大像时,把半铁半泥的脚视为“十角”,把“敌基督”视为“其中长起的小角”。打碎这像而“充满天下”的“石头”即为“从天降下来审判全世界”的基督。基督“以肉身……第一次降临……在伯利恒,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是发生在“第5500年”。(约翰福音中的描述证明这个计时法。“约有午正”标明当时已过半天。主看一日如“一千年”,因此其半截为500年)。在接下来的500年中,福音将传遍全世界。然后“6000年必须满足,以使神圣的、‘神歇了他一切创造之工’的安息日来临,”安息日是“圣徒国度”的象征,它将满足创世六日的类比性预言:[60]
“……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因为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万物,所以6000年必须满足。然而至今尚未满足,正如约翰所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即指第六个;‘一位还没有来到’。”[61]
普图伊的维多利诺斯一样期盼着“那基督与他的选民作王的第七个千年时代。”他称这个未来的国度为“那真实又公平的安息日”。他同样依据圣经中千年与一日的关联把自己的时间架构建基于创造日的类型学预言上:“因此,主将一千年归于那七日中的每一日。所以有这样的警告:‘主看一日如千年。’因此,在主的眼中,每一千年都是被立定的,因我发现主的眼有七只。因此,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基督与他的选民共同作王的真正安息日将在第七个千年时代。”[62]
奥林匹斯主教麦托丢(Methodius,公元260-312年)主张字面解经,反对俄利根的灵意主义。麦托丢提出,六天的创造之后是上帝歇了创造之工的第七天,七月为守“耶和华的节”而收藏地的出产,这都表示“当这个世界在第七个千年时代终结时,当上帝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时,他将为我们欢喜。” [63]
这里的 “节” 似乎是旧约的住棚节。对麦托丢来说,这意味着信徒的复活、离开“今生埃及”、“在复活的第一天建造自己以美德果子装扮的会幕”,为的是“与基督庆祝千禧年的安息,乃第七日,即真正的安息日。”在此之后,如同以色列人“在住棚节的安息后,来到了应许之地”,信徒们的身体将会在“一千年的时期后”由“必朽坏的肉身变为天使般的形式与美姿”并上升到“上帝天外的殿中。” [64]
拉克唐修在写给君士坦丁的《神圣原理》(Institutes)中广泛使用创造日类比的末世论来展开他关于前千禧年论的构想:
“因此,由于上帝的一切做工都在六天内完成,世界必以目前的状态持续六个时代,即6000年。正如写下‘主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的先知所示,上帝的大日为一系列的千年所规范。就像上帝在那六天内劬劳,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作品,他的宗教和真理必在这6000年里劬劳,而这6000年也是邪恶盛行并实行统治的时候。既然上帝在完成做工以后,第七日休息并赐福于它,那么在6000年完毕之时,一切邪恶必从地上除灭,正义必统治一千年。必有宁静与安息,终止这世界长久忍受的劳苦。”[65]
拉克唐修相信,就如上帝在第六天创造“属地的人”并将他放入“精心准备的家园里”一样,在当前的“第六天”,“属天的”、“真实的”、“圣洁的人”是“从上帝的道生成的”,是“用上帝的教义和戒律为正义而塑造的’。第一个人是“必死的且不完美的”,是“用尘土造成的”,要“生活在世一千年。”然而,“一个完美的人”正在“这尘世间”形成,要“被上帝复活”并“在世做王一千年。”[66] 这将在何时发生呢?当“6000年满足”的时候,“大结局的最后一天即将来临”。实际上,根据针对这一“完满之日”“所预言的先兆”,每位写过关于“自创世以来的年数有多少”这个话题的作者——尽管他们当中关于既往年数的分歧较大——但都认为剩余的时间最多不到200年(“所有的预期都不超过200年的大限”)。[67]
通过分析拉克唐修关于“七千世界”的起始和终止的谈论,我们得知他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千年国度”。他说,在“神圣统治”之初,撒旦将“被上帝捆绑”,而当这个时代临近结束时,撒旦将“被重新释放”,并将“召集列国”以“向圣城争战”。而当这个“无数国联军”“围攻这城”时,“上帝最后一次的怒气要降临在万国之上,并彻底摧毁万国。”[68]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拉克唐修之所以这么写,是基于他对圣经的信心,以及对当时年老地球哲学家们的抵制:
“如果有谁对他们有所期待,或者对我们缺乏信任,请走近天书的圣殿。让他通过信实的圣经得到更充分的教导,让他认识到哲学家们犯了错误,他们以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或者以为自创世以来会有无数的千万年。6000年尚未完结,当这个数字满足时,一切恶行终将被除去,单靠正义统治。”[69]
尼西亚会议之后的反千禧年论者
自公元三世纪开始,随着前千禧年派不再主导末世论,现存文献中提到六/七千年架构的就为数不多了。然而,该观点以新末世论的面貌幸存了下来。泰勒指出,耶柔米(约公元340-420年)和波提亚的希拉流(Hilary of Poitiers,约公元291-371年)断言,在6000年末,基督将再临,随后将是永恒的、天上的(非尘世的)国度。[70]
奥古斯丁虽然在早年拥护前千禧年论,但后来因视之为属“肉体”的学说而拒绝之。[71] 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六/七千年的地球历史架构。如上所述,他认为自创世以来一共不到6000年。[72]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奥古斯丁坚持6000年的历史观,是因为他相信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并且反对当时的年老地球观。例如,他反对埃及人所声称的对星辰的了解已经超越十万年的说法,因为他们的说法与上帝记载的历史相矛盾。在这点上,他也拒绝了其他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他们彼此矛盾:
“有人从最空洞的假设出发,反复念叨埃及人了解星辰的运行已经有十多万年,这是徒然无益的。埃及人在哪些书里有关于这一数字的记载呢?他们在两千多年前才通过其偶像伊西斯学会了识字!这一点是瓦罗(Varro)提出来的,他在历史学上有一定的权威,他这种说法也不与圣经的真理相矛盾,因为距第一个人(称为亚当)面世还不满6000年。有人要劝我们相信与确切的真理相差甚远甚至相悖的时候,我们与其说要反驳他们,倒不如说该嘲笑他们。在过往的历史学家当中,要不是那位连将来之事也曾预言过而且其预言正在我们眼前应验的他,有哪位更加值得我们信赖呢?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应该相信那位不与我们所坚持的神圣历史相矛盾的他……但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方面受到上帝权威的支持,因此毫无疑问地认定,任何与其相对立的思想都是极为错误的……”[73]
在奥古斯丁的末世论里,“第七天”不再是第七个一千年的时代,而是第二次降临之后的永恒状态。他说“第七天”指向“永生的安息日”。[74] 像伪巴拿巴(Pseudo-Barnabas)、特土良(Tertullian)和维多利诺斯一样,奥古斯丁的确提到了“第八天”,并论证教会做礼拜的星期日即“第八天”。他不承认第七天是地上的千禧年,反而强调“第八天”(一周的第一天)象征着复活和“第七天”永恒的安息:
“你如果在阅读创世记的时候检索这七天的记录,就会发现第七天没有晚上。这意味着其所象征的安息是永恒的。最初赋予的生命因人的罪孽而不能永存。然而,第七天所象征的最终安息是永恒的,所以第八天也会得到永恒的祝福。第八天接续了而不是破坏了永恒的安息,因为这安息如果能被破坏,那就不是永恒的了。因此,第八天,即一周的第一天,对我们来讲,代表着那最初的生命。不是被夺走,而是变为永恒。”[75]
在以上引文中,请注意奥古斯丁明确地使用创世记第1章的“七日”作为地球历史时代的一种预表模式;因此他肯定认为地球的创造(包括人类的创造)发生在不到6000年之前。奥古斯丁以象征着“第七日”在天堂里永恒的生命的“第八日” 作为《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结束——在地球经历了六个历史时代之后: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定义的时期把时代看作日,那么这一安息更加明显,因为这个时期就是第七日。第一个时代相当于第一日,从亚当延伸到大洪水。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为第二个时代。相同之处不是在时间长短上,而是在世代数上,即每个时代包括十代人。如福音作者马太所计算的,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临,共有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包含十四代人——分别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一个时代,从大卫到被掳的第二个时代和从被掳到基督以肉身降临的第三个时代。至此共经过了五个时代。我们目前正处于第六个时代。我们不能用任何世代数来衡量这个时代的长度,正所谓:‘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过了这个时代之后,上帝将像在第七日一样安息。那时他将赐予我们主内的安息(即第七日)。这里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地讨论各个时代,但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第七个时代将是我们安息的时代。那个时代不以晚上结束,而是以主的日子结束。主的日子就是第八日,是永恒的日,因基督复活而成圣,预示着灵魂的永恒安息,也是肉身的永恒安息。那时我们将在安息中看见【他的面】,因看见而爱,因爱而赞美。这就是无尽的结局。除了迈向永久的国度,我们还想要怎样的结局呢?”[76]
因此,奥古斯丁认为世界历史的前五个时代/日已经完成,而当时正处于第六个时代/日。无法确定奥氏是否也像之前的某些作者一样认为每个时代是精确的一千年。事实上,他似乎认为第六个时代的长短无法断定,而将由第七个时代来结束。另外,奥古斯丁认为 “第七个时代” 不属于 “这个世界” :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时,他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因全能者的大能,即使在一瞬间也能造出万物。确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并没有为享受(必要的)安息而做工,反而是为了指向他将在这世上的六个时代之后的第七个时代,如同在第七日,与众圣徒安息。众圣徒当完成服侍神的所有善工之后同样将在主内安息。这一切善工又由上帝实现;是他召唤、教导、赦免过去的罪,并称罪人为义。”[77]
请再次留意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即使在一瞬间也能造出天地及其中所充满的”。创世记的 “第七日” 指向 “第七个时代” ,即在 “这世上的六个时代之后。” 奥古斯丁明确指出,第七个时代将不在人间,而在天堂:
“神在六天之内完成创造之工,在第七天歇息。世界历史以神与人的交往为标志分为六个时期,……目前处于第六个时期,该时期将止于至高的救主为审判而再临之际。与第七日相应的是圣徒的安息——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来世,就是在地狱中受苦的财主看到拉撒路安息的地方,那里没有夜晚,因为没有衰败。”[78]
晚年的奥古斯丁可能不再完全持守六天并非字面意义的概念。事实上,他在《撤回(修订)》(Retractions Revisions))中表示,自己在《创世记的字面意义》(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中提出的问题多于“找到的答案”,而且在这些答案中,“只有少数是确信的。”[79]
因为他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答案”是确信的,我们不能断定他指的就是六日的自然属性。关键的是,即使在他对创世记采用最为寓意性的解释的时候,奥氏也坚持认为当时地球的年龄少于6000年。并且他坚信古老地球年龄的说法与上帝在圣经中的历史记载相违背。奥古斯丁是相信年轻地球创世论的主流先贤的杰出代表。
教会先贤对大洪水的认识
先贤们似乎并没有把地球年龄的概念建立在挪亚大洪水的基础上。很显然,当时在判断地球年龄时无需考量或顾及地质学方面的问题。在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地质学、大洪水和地球年龄才被纠缠到一起。目前,只需注意到大多数先贤把大洪水视为真实的全球性事件就足够了——他们论断异教中的洪水故事不是圣经中的大洪水,而是地区性洪水。
殉道士贾斯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评论。但是他确实指出:“正如圣经所说,全地都被淹没,水的高度超过了所有山脉十五肘。”[80]
安提阿教父提阿非罗(Theophilus,约115-185年)更具体地反驳过柏拉图。柏拉图曾说,大洪水“只延及平原,而非全地,而且那些逃往最高山丘的人得以自救。” 提阿非罗也不接受希腊人的诸如“杜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在“柜子”中躲过大洪水;某个叫克纽麦努斯(Clymenus)的生活在第二次大洪水的时候”等的说法。他称这些希腊人为“可怜、非常亵慢和无知的人”,并回答他们说 “我们的先知、上帝的仆人摩西在记载世界的起源时”,详细地描述了洪水如何“来到地上”——“而没有讲到皮拉、杜卡利翁或克纽麦努斯的传说;也真的没有说只是平原被淹没,或只有逃到山上的人得以幸存。”提阿非罗接着争辩说,摩西从来没有教导过第二次洪水,反而说“再也不会发生普世性洪水了;之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 提阿非罗说,摩西讲述“洪水持续了四十昼夜,”“大水高过每一座高山15肘”,而且除方舟上八人之外,“全人类”被“摧毁”。提阿非罗进一步评论大洪水,指出“方舟的遗迹至今仍在阿拉伯山区能看到”,最后提到摩西讲述的是“大洪水的历史”。[81]
早期北非三位一体派的重要神学家特土良(115-222年)断言“整个地球被大水淹没”。他的证据是“直到如今海螺等软体动物还寄居在高山上;它们急于向柏拉图证明,高山也曾与波浪共舞。” [82] 特土良还把大洪水称为 “普世的灾难,万物的终结者。” [83]
纳赞祖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公元329-389年)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380-381年),是反亚流的神学家“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格里高利指出,挪亚“受托从大水里拯救全世界”,并且“在小方舟里逃离洪水”。[84] 在肯定挪亚洪水的普世性的先贤 中,伟大的西方神学家奥古斯丁也是卓尔不群。他断言洪水是如此浩大,其水位“上升到最高山脉之上十五肘”,从而反对纯粹寓意性的解释。[85]
关于教会先贤一贯支持全球性洪水的立场,戴维斯·杨列举了更多证据。他提到,加萨的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 of Gaza,约公元465-528)在他所著的《创世记评论》(Commentary on Genesis)中,伪修斯 (Pseudo-Eustathius,生卒不详) 在他的《六日谈注》(Commentary on Hexaemeron)中,都提及在高山上发现海洋遗骸(如贝壳、各种鱼类),以此论证洪水的全球性。伪修斯声称鱼类定然是“被泥土裹挟才汇集到山洞里的。” 戴维斯·杨指出,伪贾斯汀(Pseudo-Justin)(大概是赛勒斯的西奥多雷特,Theodoret of Cyrus,约393-466)是唯一提议洪水可能是局部性的教会先贤。[86]
结论
教会先贤对创造的讲论不胜枚举。对他们而言,创世记时间顺序的框架预示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直到末日。他们看到,受造界秩序的起源隐含着对现在和未来的预期。而且,在地球年龄的问题上,教会先贤立场鲜明地反对当时的自然主义哲学:
1. 教会先贤写作的形势下充斥着自然主义的宇宙起源思想,其中大多数理论认为地球是非常古老的,甚至是永恒的。即便这些哲学家提出有智能的起因,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上帝,先贤们依然把这些思想家看作无神论者。
2. 大多数先贤使用经文中关于创世的权威性记载来反驳当时的自然主义起源理论。亚历山大学派比较容许使用科学研究的论证,但他们依然把圣经看作支持自己关于上帝创造过程的观点的最终权威。
3. 我们已经表明,大多数教会先贤坚持创造日为字面上的每天24小时的日子。至少他们都认为创造是突然发生的。我们陈明了没有任何一位先贤提出过任何肯定深度时间的说法。这与休·罗斯的宣称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逻辑上讲,如果哪位没有说明每个创造日的确切长度,甚至将其视为纯粹的象征意义,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不看重创造的时间框架,或者把深度时间当作一个可行的选择。经常列为反例的克莱曼特、俄利根和奥古斯丁——他们的观念要以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学为背景来理解 ——他们都认为创造是在一瞬间内完成的。
4. 尽管先贤们对创世记第1章采取的诠释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坚持了六日预表六/七千年的类型学末世论。他们传统上认为创世发生在不到6000年之前,6000年结束时主会再临,世界将会终结或发生剧变。
5. 先贤们断言,创世记第6-8章中的洪水是全球性的,有的还认为化石的存在是这一灾难的证据。
6. 先贤们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
7. 先贤们并不追求新颖。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梳理、凸显并保存使徒留下的古老正统教义。
教会先贤的著作能为当今的基督徒带来启发。先贤并不完美,但他们曾把圣经视为最高权威的上帝话语而寻求与其进行虔诚的互动,并阐明了三位一体和基督位格这两条基础性的正统教义。他们在教义方面的工作体现在与圣经共鸣的信条里,这些信条在今天依然对福音派教会发挥着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假定教会先贤关于地球年龄、创造周和普世性洪水的思想不如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甚至已经被科学所取代。如上所示,既然教会先贤们笃信圣经真实地教导地球是在数千年以前用字面上的六天创造的,而且洪水是普世性的大灾变,他们的见解更应该得到尊重。先贤们在面对当时的自然主义进化理论时,因为确信那些概念是根植于异教,而非圣经,所以坚定地持守基于圣经的宇宙起源观。我们想,神会喜悦教会认同并听从约翰金口(John Chrysostom)1600年前写下的话语:
“不信服圣经的教导,却引入自己头脑中的异想——我相信如此做法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创世记讲道集》(Homilies on Genesis,XIII,第3页)。
[1] 感谢余理斐(Thane Ury)对本章最后定稿的大力帮助。
[2] 关于教会先贤的可用资源很少。最近的一个亮点是由 InterVarsity Press出版的大型著作The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Project,总编辑是托马斯·奥登(Thomas Oden)。这部 28 卷的丛书呈现了公元749年前教会先贤对圣经的注释。此著作对于每一位渴望充分了解历史遗产的福音学者或基督教徒是必不可少的。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完全撇开现代潮流的羁绊(请参见下面的注释12),采样展示什么是对启示的上帝和上帝的启示的敬重。以749年为界并非随意,这是约翰·达马森(John Damascene) 逝世之年,标志着东方先贤时代的终结。西方先贤以伊西多尔(Isidore)逝世之636年为止点。
[3] Ad fontes, (回归源泉)对基督徒来讲,在现代就像在过去一样重要。
[4] Hugh Ross and Gleason L. Archer, “The Day-Age View” (and responses to the 24-hour view and the framework view), in David G. Hagopian, ed., The Genesis Debate: Three Views on the Days of Creation (Mission Viejo, CA: Crux Press, 2001).
[5] Hugh Ross, A Matter of Days: Resolving a Creation Controversy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2004) p. 48–49. See also Creation and Time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4), p. 24.
[6] Hugh Ross, The Fingerprint of God (Orange, CA: Promise Publishers, 1991, 2nd ed.), p.141
[7] Ross, Creation and Time, p. 24.
[8] Ross, Matter of Days, p. 49.
[9] 在寻找进化论的前身时, Henry Osborn 惊讶地发现许多达尔文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见Henry F. Osborn, 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 2nd e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p. xi; cf. 41–60 and 91–97).
[10]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547年)相信人类是鱼类的后代;而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公元前490–435) 则被称为 “进化论之父”。见Richard Lull, Organic 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 6.
[11] Basil of Caesarea, Hexaemeron 1.2 in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Philip Schaff, Henry Wace, eds., 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Series 2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4) vol. 8. (随后简称为NPNF2)。当我们把当前关于起源的科学理论当作解经的认识论根基时,应当思量巴西流关于自然主义理论之短命的言论。
[12] Lactantius, Institutes 7.14, in ANF, vol. 7
[13] 虽然教会先贤面对的挑战与今天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挑战也不小,因为他们也一样会变成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产物。空气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强力哲学思想与文化压力。这些因素对每一位先贤的神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候只能从迹象中推断。总之他们的思想都不是在密封的环境下形成的。除了他们自己在成长和训练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其时代背景中总有新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诺斯底主义、摩尼教、希腊罗马密教、多神论等多种哲学思想、邪教和基督论异端的威胁。
[14] 像特土良、俄利根和优西比乌等思想家可归类为教会学作者。在本章,为了方便,“先贤”一词用的范围比在研究教会先贤本身时更为广泛。
[15] Davis A. Young, Christianity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p. 19 and 22.
[16] 许多人虽然未明确地提出24小时的长度,但其作品也似乎很自然地把每一日理解为普通的太阳日,因为他们把创世记第1章的其余词语都按字面意思理解。见 Theophilus of Antioch (c. A.D. 115–168–181), To Autolycus 2.11–12); Methodius (A.D. 260–312), The Banquet of the Ten Virgins 8.11; 9.1; Epiphanius of Salamis (A.D. 315–403), Panarion 1.1.1.; Cyril of Jerusalem (c. A.D. 315–386), Catechetical Lectures 12.5.
[17] Lactantius, Institutes 7.14, in ANF, vol. 7. 整段引述见上文。
[18] Victorinus,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in ANF, vol. 7. p. 341
[19] Ephrem the Syrian, Commentary on Genesis 1, quoted by Seraphim Rose, Genesis, Creation and Early Ma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Vision (Platina, CA: Saint Herman of Alaska Brotherhood, 2000), p. 101.
[20] Ephrem the Syrian, Commentary on Genesis 1.1, in Kathleen E. McVey, ed., Ephrem the Syrian: Selected Prose Works, trans. Edward G. Mathews and Jospeh P. Amar, i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FC hereafter) (Washington, D.C., 1961), 91:74.
[21] 六日谈体裁包括专论、讲道和解经,按照创造的六日安排内容,其中有的是释经类,有的是比较寓意性的。六日谈包括所有的关于创世记中的创造记载的作品,有正式的、有二级文献,也有诗歌。六日谈文学在17世纪以前颇受欢迎,也成为了一些教会先贤特别关注的体裁,尤其在四旬斋期。许多作者都效仿巴西流九堂讲道的模式。巴西流的兄弟,尼撒的格理高利(Gregory),及安波罗修(Ambrose)都有六日谈的著作。关于巴西流之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六日谈作者,如卡尔齐地乌斯(Chalcidius)、犹太人斐洛(Philo Judaeus)、希坡律陀(Hippolytus)、帕皮亚斯(Papias)、潘代诺(Pantaenus)等,以及许多其他后期的六日谈作者,请参见Frank Egleston Robbins, The Hexaemeral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ommentaries on Genesi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22] Basil, Hexaemeron 9.1, in NPNF2, vol. 8.
[23] 同上,2.8, in NPNF2, vol. 8.
[24] 同上。休·罗斯和车理深曾断言在下一段能找出巴西流容许创造日可能长于24小时的证据,但他们错了。巴西流强调的关键是“一日”与永恒时间(“世世代代”)的分别。巴西流先前的论述仍然限定了 “一日”为24小时。这是相关的段落:“但我们是否必须为此假设神秘的因由呢?上帝造出了时间的本质,测定了时间段,用日子作为划分时间的尺度。为了用星期作为另一个时间长度,他让星期自我轮回以计算时间的进程,并规定日子轮转七次为一个星期:周而复始。永恒的本质也是如此,自我轮回,无休无止。那么,假如时间之初被称为‘一日’而不是‘头一日’,也是因为圣经意欲描述其与永恒之间的关系。其实,将与其他日子完全独立并分割出来的那一天称为‘一日’是恰当而且自然的。如果圣经要对我们说许多时代,就会说‘世世代代’,而不会将之列成第一、第二和第三。由此可见,这里呈现给我们的不是时代的界限、起始和循环,不是神的作为的各个阶段及各种方式的分界。”见Ross and Archer, “The Day-Age Reply,” p. 205。莱森(Robert Letham)似乎认为,巴西流关于一日24小时的概念和他所说的一切是在“不到一瞬、迅速到无法察觉的刹那间所创造” (1.6)有冲突。不过,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要留意巴西流如下的观点即可:上帝先把一切的根本创造出来,然后再用七天给与形状。他认为“起初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是瞬间发生的”。见Robert Letham, “‘In the Space of Six Days’: The Days of Creation from Origen to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WTJ 61 (1999): p. 152–153。
[25] Thomas Torrance很好地总结了巴西流观点的历史意义:“宇宙与其理性秩序绝对相关的基督教概念正是【巴西流】宇宙学观念的根本。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出了人类思想并恩慈地使其与他自己超越的思想维持独特的关系,这是对古希腊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核心概念。巴西流六日谈里的这些概念意义重大,他不仅挑战了对有形和无形的现实世界的古典见解的理性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希腊思想的转化,甚至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留下了印记。” Thomas F. Torrance, The Christian Frame of Mind: Reason, Order and Openness in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 (Colorado Springs, CO: Helmers and Howard, 1989), p. 5.
[26] Gregory of Nyssa, Hexaemeron, trans. Richard McCambly, in J.P. Migne, ed., Patrologia Graeca (Paris: Migne, 1863), 44:68–69.
[27]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6.16, in ANF, vol. 2.
[28] Origen, Contra Celsus 6.60, in ANF, vol. 4: “我们尽力答复了对上帝‘指令第一、二、三个事物产生’的异议。为此引用了‘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明直接的造物主,乃世界的创造者,正是道,是上帝的儿子;而道之父命令自己的儿子,道,来创造世界,是首位的造物主。关于第一日造光、第二日造穹苍、第三日天下的水聚集成几个大水库(因而地发生仅受大自然控制的果子)、第四日造光体和众星、第五日造水生动物、第六日造陆生动物和人,我们在创世记注释和前几页详细地谈过,并反对那些按表面上的意思来理解神的话语、说世界的创造是在六天内发生的人。为此曾引用下面的话:‘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 神造天地的日子。’” 关于俄利根三分法的“三重”诠释学,另参见4.11–13。Jean Daniélou告诫我们,俄利根在现实中的做法比他在理论上更加有寓意性,见Bernard Ramm,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3r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0), p. 31–33. 比较Louis Berkhof, 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50), p. 20.
[29] Origen, De Principiis 4.1.16 (Greek translation), in ANF, vol. 4; Ross, Matter of Days, p. 44.
[30] Origen, Contra Celsus 6.61 in ANF, vol. 4:“……在创造万物完毕后,上帝歇工的安息日只要世界存在就一直持续。凡是在六日内完成了自己的工、没有忽略他们的任何任务的人,他们的灵性将在安息日提升,思考属灵的事物,加入公义有福之人的会堂,并与上帝一同庆祝。”
[31] Origen, De Principiis 4.1.16 (Greek translation), in ANF, vol. 4.
[32] 同上,1.19。
[33] 同上,1.20。
[34] Letham, “‘Space of Six Days,’” p. 151–152.
[35]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85, 153–154.
[36] Ambrose, Hexaemeron 1.10.3–7, in Ambrose, Hexameron, Paradise, and Cain and Abel, trans. John J. Savage, in FC (Washington, D.C., 1961), 42:42–43.
[37] Jack P. Lewis, “The Days of Creation: An Historical Survey of Interpretation,” JETS 32 (1989): p. 440–444. Lewis对奥古斯丁观念的综述是我这里的提要的主要基础。又见Letham, “ ‘Space of Six Days,’ ” p. 154–157; Bradshaw, “Creation and the Early Church,” chapter 3, www.robibrad.demon.co.uk/Chapter3.htm.
[38] Lewis, “Days of Creation,” p. 440.
[39] Louis Lavallee指出,奥古斯丁瞬间创造观的来源是对七十士译本西拉书18:1的错误翻译:“根据翻译家 J.H. Taylor的说法(The Literal Meaning1. 254),拉丁文版本中‘simul’一词(同时,一同)看似是希腊文‘koine’(通常,无例外)的误译。耶柔米(Jerome)因为不接受旁经,没有重新翻译西拉书,所以如今的拉丁通俗译本仍包含最早的拉丁译文。” (Louis Lavallee, “Augustine on the Creation Days,” JETS 32 (1989): p. 469-61, n. 20) 因为克莱曼特和巴西流都持有基于创世记2:4的类似观点,所以这种观点不可能是奥古斯丁的发明。
[40] Augustine, Confessions 13.33.48, in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Philip Schaff, Henry Wace, eds.,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ries 1 (NPNF1 hereafter) (re-print ed.; 14 vols; Hendrickson, 1994), vol. 1: “因此,早晨晚上交替,半明半暗。是你由无而创造,未由你,未由非属你之物,或前所创造之物,而是由你同时所造之实物,是你在没有任何时间间隔的过程中把无形的形成。因天地之物质统一,天地之形体不一,是你由无而创造出物质;但世界之形体你却是由无形之物质造成。都在一时,让形体无间隔地随物质。”
[41] Lewis, “Days of Creation,” p. 441–442.
[42] Jonathan Sarfati, Refuting Compromise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 p. 118. 希伯来圣经中 םֹוי(yôm) 和 עַגֶר(rega‘) 之间的区别,也见Jim Stambaugh, “The Days of Creation: A Semantic Approach,” Journal of Ministry and Theology 7 (Fall 2003): p. 61–68.
[43] Augustine, City of God 11.6, in NPNF1, vol. 2: “如果神圣而无误的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以便让我们理解到,他在此之前没有进行过创造——因为如果说他在之前创造过,那么之前所创造之物才值得被称为‘起初’所造——那么,可以肯定,世界没有在时间之内被造,而是与时间一同被造。因为凡是在时间之内创造的一定是在某个时辰之后、某个时辰之前——即在过去的之后和将来的之前。但是不存在过去,因为时间是通过受造物的运动来衡量的,而那时还没有受造物。如果说,从头六七日的次序可以看出,随着天地的创造,变化与运动也被创造,那么,世界是与时间同时被造的。在那几天里,早晨和晚上被计数,直到第六日,上帝完成了万物的创造,第七日奥秘地、奇妙地标志了上帝的安息。这些日子究竟如何,是我们难以想象,更难以言表的!”
[44] Lewis, “Days of Creation,” p. 441–442; Augustine, City of God 11.33, in NPNF1, vol. 2: “……首先,是概括介绍创造的过程,随后根据神秘的天数列出每个阶段。”
[45] 总体而言,大多数早期先贤都依靠七十士译本或拉丁文译本,而不了解希伯来语或亚兰语(俄利根和优西比乌例外),并且对闪族人的思维方式不大熟悉。
[46]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12.10, in NPNF1, vol. 2.
[47] 同上,12.12。
[48] 年老地球和年轻地球的创造论者必须立定心志,在使用和信任奥古斯丁或任何其他先贤的权威上要前后一致。显然,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引用、信任或模仿先贤。恰恰相反,本书的主题正是“回归源泉”。我们知道上述规则同样适用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所引用的先贤。我们只是提出一个适当的建议,即要负责任地引用过去的杰出人物,而不是断章取义或随意取舍。先贤的权威很宝贵,但是当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论点相悖或相反时,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
[49] 这一段与休·罗斯和车理深相抵触。他们认为:“殉教者贾斯汀、里昂的主教爱任纽、拉克唐修、普图伊的维多利诺斯和奥林匹斯的麦托丢(Methodius of Olympus)都明确地支持创造日代表六个连续的千年时代。”(Ross and Archer, “The Day-Age Response,” p. 69; see also Ross, Matter of Days, p. 45). Duncan和Hall指出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J. Ligon Duncan III and David W. Hall, “The 24-Hour Reply,” The Genesis Debate, p. 99–102)。在这一段讲到的先贤并没有讲每个创造日的长度是1000年,而是指出创造日从类型上预表着后来世界历史的六个时代,每个时代有1000年。另参Sarfati, Refuting Compromise, p. 114–122.
[50] D.T. Taylor, The Voice of the Church on the Coming and Kingdom of the Redeemer: or, a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Reign of Christ on Earth (8th ed.; Albany, OR: Ages Software, 1997), p. 32–36. 第八版是1866由Scriptural Tract Repository 出版。
[51] “卡巴拉” (希伯来语 לבק “接受”) 基本上是源于犹太拉比的一套古代神秘主义文献,指基于对希伯来圣经的一种秘传的解释,其中含有诸多泛神论因素。卡巴拉的秘传教义今天在“极端正统”的哈西迪派和路巴维奇派犹太教中仍可见到。
[52] Arnold D. Ehlert, “A Bibliography of Dispensationalism, Part 1” BSac 101 (January 1944): p. 99.
[53] Alfred Edersheim,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 (2 vols.; reprint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7), 2:738.
[54] Justin Martyr, Dialogue with Trypho, p. 80, in ANF, vol. 1.
[55] 同上,第81页。全文引述如下:“亚当被告知,他在吃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必定会死。因而,我们知道他没有活满一千年。另外,我们意识到‘主看一日如千年’的说法和这个主题有关联。再者,名叫约翰的那位基督的使徒,曾与我们同在。他依靠神对他的启示预言过,凡信我们的基督的将在耶路撒冷居住一千年,此后将发生普遍性的、永恒的复活,全人类受审判。”贾斯汀没有说创造的第六日要持续一千年,而是说亚当如果吃树上的果子,就会在他所生活的当日的时间限制(1000年)之内就会死去。把贾斯汀当作长日论的先例并不合理(反驳Ross and Archer, “Day-Age Reply,” p. 204; Ross, Matter of Days, p. 43)。关于休·罗斯和车理深引用的爱任纽在《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 5:23.2中的言语,也可以作出类似的答复。爱任纽没有认为创造的第六日为1000年。他的意思是:第六日,即亚当被造的那一天是他自己的1000年的日子的开始。在那一天,亚当成了对死亡的债务人,没有活到他自己的日子(1000年)的尽头。参见Bradshaw, “Creationism and the Early Church,” www.robibrad. demon.co.uk/chapter3_pf.htm. 据说贾斯汀认为,因为创世记第1章里的第七日没有写“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这“意味着在那日未尽的时候大结局即将发生。” — Fragments from the Lost Writings of Justin 15 (ANF, vol. 1) —Anastasius文选.
[56] Epistle of Barnabas, p. 15, in ANF, vol. 1: “关于【耶和华】在西奈山面对面交代给摩西的十诫中的安息日有以下记载:‘手洁心清地将耶和华的安息日分别为圣。’ 另外有说:‘我的儿子们只要遵守安息日,我将使我的怜悯安息在他们身上。’安息日在创造之初就被提及:‘六日之内上帝创造他手之工,在第七日完毕,并安息,并赐福给第七日。’ 我小子们啊,注意到这个说法的意思,‘他在六日内完成的。’因主看一日如千年,这就意味着主将在六千年内完成一切。他亲自作证说,‘看哪,今天将如一千年。’因而,小子们,六日之内,就是在六千年后,一切将结束。‘在第七日安息了’是指:当上帝之子【再】 来临,他将毁灭恶人的作为、审判不敬虔的人、使日月星辰改动。在那时,他将是真正的安息。‘月朔和安息日我不能容忍。’请意识到上帝如何表达:你们目前过安息日的方式我不能接受,但这就是我所做的,【即】当使一切都安息时,我会让第八日作为新的开始,即是新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欢心地守住第八日,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
[57] Larry V. Crutchfield,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Dispensationalism: Dispensational Concepts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Conservative Theological Journal 2 (1998): p. 258–259.
[58]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5.28.2-3, in ANF, vol. 1.
[59] 同上,5.30.4。另见5.33.2; 5.29.2。
[60] Hippolytus, On Daniel 2.3-6, in ANF, vol. 3. 其他先贤同样给出了地球的具体年龄:安提阿的提阿非罗(约公元180年)说是5698年(To Autolycus 3.28);迦太基的居普良(约公元205–258)认为“自从魔鬼首次袭击人类以来,已经过了将近六千年。”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11); 朱利叶斯·阿弗里卡纳斯(Julius Africanus, 约公元200–232–245)以5500至5531为第一次降临的年代(The Extant Fragments Of The Five Books Of The Chronography Of Julius Africanus 1; 18.4)。有三位非前千禧年论者也给出了地球的具体年龄:亚历山大的革利免说是5592 年(Stromata 1.21);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约公元270–340)说是5228年(Chronicle);希波的奥古斯丁在City of God 12:11也提到地球年龄。参见Bradshaw, “Creationism and the Early Church,” chapter 3, Table 3.4, www.robibrad.demon.co.uk/Chapter3.htm.
[61] Hippolytus, On Daniel 2.4, in ANF, vol. 3.
[62] Victorinus of Pettau,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in ANF, vol. 7.
[63] Methodius, The Banquet of the Ten Virgins (or Concerning Chastity) 9.1, in ANF, vol. 6.
[64] 同上,9.5。
[65] Lactantius, The Divine Institutes 7.14,in ANF, vol. 7.
[66] 同上。
[67] 同上,7.25。拉克唐修相信这些事只有在罗马城陷落之后才会发生。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恳请上帝延迟“那可憎的行出如此大事的暴君的到来,并挖出那只眼睛,因他所行的毁坏,世界本身将遭受灭顶之灾。”(要记住拉克唐修是在为皇帝服务。他对罗马的态度与此前大迫害的时期大不相同!)拉克唐修不认为罗马城将再持续太久。
[68] 同上,7.26。
[69] Lactantius, Epitome of the Divine Institutes 70, in ANF, vol. 7.
[70] Taylor, Voice of the Church, p. 82–84.
[71] Augustine, City of God 20.7ff., in NPNF1, vol. 2. 注意奥氏之前是 “千禧年论” 者,后来发生了变化:“福音作者约翰在启示录里谈到了这两次复活。但一些基督徒不理解他所提到的第一次复活,因而用各种荒谬的幻想来解释这些经文。正如使徒约翰在上述书卷中所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凡是根据这段经文的信息而猜测头一次的复活是将来的、是肉身的人,主要是为一千年这个数字所感动(也有其他的理由),他们认为圣徒应当在那个时期享受一种安息。他们考虑到人类从被造后辛苦了六千年,当年因罪孽而被逐出乐园去面对凡人的祸患,所以享受神圣的休闲是应该的。正如经上所写的那样,“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们认为如同六日后有安息日,那么,在六千年后也应有千年的安息。而圣徒们正是为了庆祝这些安息的日子而复活。如果说众圣徒在安息时的喜乐是属灵的并来自于上帝的同在,那么这种观点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自己也曾经持有这种观点。不过,既然他们断言凡在那个时候复活的人都会享受过度的、属肉体的闲暇宴席,其酒池肉林不仅让有节制的人震惊,而且也不可思议,只有属肉体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宣称。我们称相信这些的人为千禧年论者。一一地驳斥这些观点太烦琐,不如着手展示应该如何理解这段经文。” 关于奥古斯丁对第二次降临前7000年正常结构的改变,另参见诗篇6.1。
[72] 见注44和45的引文。
[73] 同上,18.40。
[74] Augustine, Confessions 13.36.51, in NPNF1, vol. 1.
[75] Augustine, Letter 55: Part 2 of Replies to Questions of Januarius 9.17, in NPNF1, vol. 1.
[76] Augustine, City of God 22.30, in NPNF1, vol. 2.
[77] Augustine, The Catechising of the Uninstructed 17.28, in NPNF1, vol. 3.
[78] Augustine, Reply to Faustus the Manichaean 12.12, in NPNF1, vol. 4. For this period, see also Sermon 75.4 (vol. 6); Tractates on John 15.6, 9 (vol. 7).
[79] Augustine, Revisions 2.24, in John E. Rotelle, ed., On Genesis, trans. Edmund Hill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2002), p. 167.
[80] Justin Martyr, Dialog 138, in ANF, vol. 1.
[81] Theophilus of Antioch, To Autolycus 3.18-19, in ANF, vol. 2.
[82] Tertullian, On the Pallium 2, in ANF, vol. 4.
[83] Tertulliam, On the Apparel of Women 1.3, in ANF, vol. 4.
[84] Gregory of Nazianzus, Second Theological Oration 18, in NPNF2, vol.
[85] Augustine, City of God 15.27 in NPNF1, vol. 2. 有关教会先贤和大洪水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radshaw, “Creationism and the Early Church,” chapter 6, table 6.1. 在线: www.robibrad.demon.co.uk/Chapter6.htm
[86] Davis A. Young, The Biblical Flo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p. 26–27.